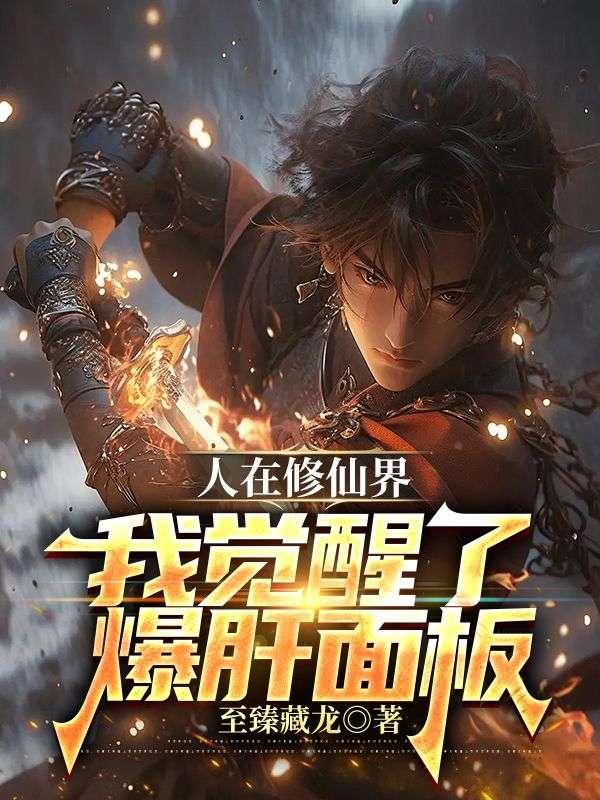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折青欢短剧全集在线观看 > 第90章(第1页)
第90章(第1页)
踏入书房,只见萧敖眉宇间透着喜色,与往日大不相同。见他进来,萧敖指了指案前的紫檀木椅:“坐。为父有要事相商。”
萧秋折缓缓落座,虽近来父亲待他亲厚,可他心中那根刺却始终未能拔除,母亲当年受的苦楚,不是如今这点温情就能抹平的。
“不知父亲唤儿臣前来,所为何事?”他声音低沉。
萧敖拿起一本册子册子递到他面前:“关于付家的罪证,为父已悉数查实。本可一击毙命,但我却不想让付家就此倒台。”
萧秋折抬眉,只见父亲继续道:“只要付家还在摇摆,就能牵制皇上心神。届时朝野动荡,民心不稳,我们便可争取更多时日筹备。我已安排你二弟、三弟分别入主户部与吏部。如此,朝中要职皆在我们掌控之中。这些年浑浑噩噩,是时候做些事了。当年被人夺走的,为父要尽数讨回来。”
夜风穿堂而过,吹得烛火摇曳不定。萧秋折望着父亲映在墙上的影子,忽觉那轮廓竟有几分陌生。
萧敖望向萧秋折,继续道:“为父自然也需要你的助力。如今你在兵部掌权,麾下精兵强将,若我们父子齐心,何愁不能为天下谋个清明世道?”
萧秋折虽早知父亲有异心,却不想他竟打算即刻起兵谋逆。父亲离朝多年,甫一归来就要行此险着,实在令人心惊。朝堂局势诡谲,岂是当年可比?皇家根基,又岂是轻易能撼动的?
“父亲。”他声音发紧,“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萧敖知晓他谨慎,道:“你且宽心。朝中不少旧部已暗中归附。如今太后干政,皇上受制于付家,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个月后,我们从贺州起兵,直取京城,你以为如何?”
萧秋折皱眉,父亲竟想在一个月后攻打皇城?
“父亲三思。”萧秋折声音陡然冷了下来,“此事非同小可,绝不可以盲目。皇家根基岂是轻易能撼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年几位皇子夺嫡之时,血流成河、民不聊生的景象,父亲都忘记了吗?如今好不容易天下安定,谁又愿再见动荡?”
“当今圣上虽受付家掣肘,又屡屡打压我们亲王府,但治国理政尚算勤勉。若没有治国之才,即便坐上那个位置,又能如何?”
他抬眸望向萧敖:“儿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先保全自身,稳固我们亲王府的势力,不再任
人宰割。我如今收复边关五城,在朝中已今非昔比,皇后与太后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但我也明白,只要我们还在这朝堂之上分一杯羹,皇上就绝不会放松警惕。”
“若此时起事,少则一年,多则数载,朝野动荡,民不聊生。儿子要对妻子负责,父亲也要为这一家老小着想。恳请父亲三思。再说那张攸年,父亲如何能确定他是真心相助,而非皇上派来的细作?我们不如静观其变。待看清局势,再作打算不迟。”
“我如今虽掌兵权,却也不是能随意动用的。即便我们真能夺得大位,这些将士百姓自当拥戴。可若事有不成,以兵权谋逆的罪名,是要遗臭万年的。”
萧秋折有自己的打算和顾虑。
萧敖手中茶盏轻轻落在案几上,道:“这些你且放心,为父心中自有分寸。你只管按自己的谋划行事便是。”
萧秋折没做声。
萧敖见他不愿多谈,摆手让他下去。
萧秋折起身,提醒道:“张攸年此人还望多加提防。莫要因一时意气,中了他人算计。”
萧秋折向来谨慎,他也猜出,张攸年应该不单单只是想和晚青妤在一起那么简单。
关于张攸年萧敖没有多提,只是“嗯”了一声。
转眼到了六月。
这几日萧秋折一直住在乔家大院,亲自照料外祖母汤药。他命人将外祖母平日的用药悉数更换,又请了太医院退下来的老御医重新诊治。经他这般精心调养,外祖母的身子骨渐渐硬朗起来,已能下床走动了。
萧秋折虽在吏部和大理寺都有要职,公务繁忙,却仍每日抽空侍奉汤药,他这般贴心,着实让外祖母感动。
他实在太忙,晚青妤来探望时,也只能与他匆匆打个照面。
奇怪的是,晚青妤这些日子过来竟一次都未遇见张攸年。
这日,晚青妤在街市采买东西时,忽听得几个商贩在巷口窃窃私语。
“听说了吗?亲王府的萧世子,根本不是亲王爷的骨肉。”一个卖绢花的妇人压低声音道。
“胡说什么?”旁边茶摊的伙计瞪大眼睛,“你看那眉眼气度,活脱脱就是年轻时的王爷。”
绢花妇人神神秘秘地凑近:“我听说啊,当年他娘跟小叔子有些首尾,后来那小叔子就莫名其妙死了。你们细想想,王爷为何这些年对自己的妻儿如此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