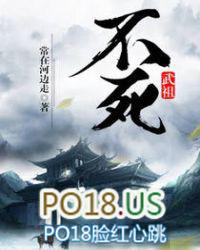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折青欢大结局 > 第56章(第3页)
第56章(第3页)
“那不然呢?”萧秋折提起茶壶,倒了杯茶递给他,“我母亲去世,我无依无靠,难道我的外祖父,我的舅舅,我的表哥不该帮衬我一把?”
陆临嗤笑一声,接过茶盏,喝了一口:“好好好,帮你帮你,不然你又得去姑母那儿告状,让我睡不安稳。”
他把茶杯搁在桌上,起身道:“不与你多说了,你自己调理调理心情,振作起来。后头的事儿还多着呢,你那情敌怕是还要找麻烦。我听说晚青桁被调到了付大人身边,也不知在布什么局,你多留个心眼。”
提到付钰书,萧秋折眉头一皱,显然不愿多提。
陆临摆摆手走了。
他走后,萧秋折又在桌前坐了会,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书柜上。那里放着晚青妤的宝贝箱子,她回晚府时没有带走。
他盯着箱子,心中挣扎良久,终是站起身来,将箱子取下,放在桌上。他掏出匕首,撬开锁扣,把箱子打开。
箱子里装了许多物件,他一眼便瞧见了那块格外显眼的玉佩。他盯着玉佩,心中惊愕不已。将玉佩拿起,仔细查看,果然与小皇子身上的那块一模一样。
小皇子那块是左半边,而他手中这块是右半边,两块玉佩显然是一对。若这玉佩真是晚青妤的,那她极有可能就是皇贵妃失踪的女儿,而他们之间确有血亲关系。
细细回想,皇贵妃当年失踪的女儿与晚青妤的年纪相仿。他记得皇贵妃生下女儿后,他曾随太妃前去探望,那时的小娃娃白白胖胖,甚是可爱。后来不知为何,那孩子突然失踪,再无音讯。
他记得那孩子的生辰,与晚青妤的似乎并不相符,但生辰可以作假,谁又知道晚青妤的真实生辰究竟是何时?
想到此处,萧秋折只觉后背一阵发凉。可转念一想,若晚青妤真是皇贵妃的女儿,为何皇家查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未曾找到她?
还有一种可能,晚青妤手中的这块玉佩并非她的,而是另有其人。这玉佩究竟从何而来,只有晚青妤自己清楚,而她却始终不愿告知。
萧秋折将玉佩放回盒中,又见盒底放着几封信,信封上皆写着“钰书”的名字。这是付钰书写给晚青妤的信,里头究竟写了什么,他无从得知。他拿起信,心中挣扎着,想要拆开一探究竟,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这样做。他压着好奇,又将信放回原处。
里面还有一片金叶子,那是他七年前送给晚青妤的,她一直珍藏着。她还说自己并非念旧之人,可若真不念旧,为何还留着他送的金叶子,甚至留着付钰书写给她的信?
她撒谎。
萧秋折顿时心生醋意。
除了那三样他认得的物件,箱子里其余的东西皆是晚青妤的私人物品。萧秋折略略翻看了一番,便将箱子重新盖上,上了锁,放回原处。
做完这些,他又走回桌前坐下,只觉得心口发颤。他不明白付钰书为何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除非他曾经见过这块玉佩,也见过小皇子身上的那块,才猜测出其中关联。若真如此,付钰书或许也并不知晓晚青妤的真实身份。但七年前的那桩旧事,他竟也知晓得一清二楚,挺让人毛骨悚然。
付钰书好像对很多事情了如指掌,只是他近两年很少留居京城,又从何得知?
萧秋折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心中隐隐不安,便唤来方齐,吩咐他安派人暗中跟踪付钰书,查探他的一举一动。
——
太后因顾及颜面,压下了萧秋折违逆圣旨之事,故而此事并未传扬出去,连晚青妤也未曾听闻。
自那太监离去后,晚青妤便一直坐在窗前,望着院中的大雨。从上午到下午,又从下午到夜晚,她看着小雨渐渐变成大雨,大雨又化作暴雨,直至深夜,再到次日清晨,他始终未曾回房休息,只是静静地坐着,仿佛在等待什么,又仿佛在逃避什么。
签完和离书后,太监定然已去了亲王府,逼萧秋折签字。如今一日已过,亲王府那边却毫无动静,想必他也签了吧。
那晚他离去时,怒气冲冲,定是对她失望至极。可这又能怪谁呢?终究是她当时太过绝情,伤了他。
晚青妤这一日一夜未曾合眼,也未曾进食,只是呆坐在窗前,目光空洞地望着外头。两只眼睛肿得如核桃一般,却浑然不觉。
玉儿忧心她的身子,端了饭
菜过来,又拿了煮熟的鸡蛋,轻轻为她敷在红肿的眼上。见她憔悴不堪,精神恍惚,玉儿温声劝道:“小姐,先去用些饭吧,身子要紧。二公子一直惦记着您,一遍遍问您如何了,就怕您不吃不睡,糟蹋了自己的身子。您就算不为自己,也得为二公子想想,如今他正是艰难的时候,您若再有个好歹,岂不是让他更忧心?”
晚青妤只觉胸口如堵了一口淤血,疼得厉害,连呼吸都变得艰难。她微微动了动身子,只觉得浑身麻木。她对玉儿道:“玉儿,帮我端杯茶吧,我实在没有胃口,只想喝口水。”
玉儿连忙去倒了杯温热的茶,递到她手中,道:“小姐,先喝点茶缓一缓,待会儿再用饭。”
晚青妤接过茶杯喝下,温热的茶水入喉,身子稍稍暖和了些。
玉儿正欲再为她敷眼,却听外头有小丫鬟匆匆跑来,禀报道:“小姐,付公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