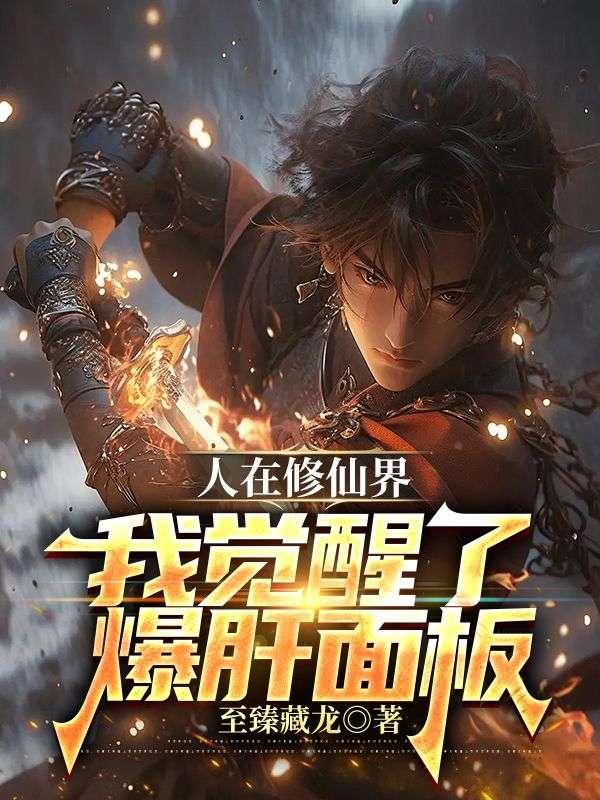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这万人迷剧本在演我[穿书 > 6大宅门06(第1页)
6大宅门06(第1页)
转天过去。
安康路,沪城人尽皆知的西式俱乐部一条街。非有权有势,背景深厚者,轻易不敢踏足。
尽管紧临租界,可恰在安康路最繁华的地段,仍有一栋古朴的中式酒楼伫立于此,望江楼三个大字显眼提名于楼上。
……
望江楼顶层。
门口侍立的人将大门拉开。阮逐舟收起玉佩,踏入屋内。
屋内一应是中式的典雅陈设,正中央八仙桌旁坐着一个穿着马褂布鞋的中年男子。
阮逐舟进了屋,男人连看都没看,将手里的鼻烟壶盖上,递给屋内站着伺候的小厮。
男人终于瞭了他一眼:“叶家的,新姨太?”
一个疑问句,却是肯定而嘲弄的语气。
阮逐舟没有配合这句玩笑笑出来,平静地看着对方。
“望江会的一把手,武凭勋先生,”他说,“今日得以一见真容,实在是阮四的荣幸。”
武凭勋敛了些笑意,正过身子,上下打量他。
“看在你有玉佩的份儿上,底下的人给你脸,让你再一次到我跟前儿说上句话。”武凭勋不紧不慢对他一扬下巴,“你来,许是为了叶家的事。”
屋内唯一新式的就是那台西洋钟,钟摆来回滴滴答答。
阮逐舟:“阮四斗胆问一句,从前和武先生做的交易,是否作数?”
武凭勋懒懒挥手,示意小厮退下。待人离去,他换了个舒服的坐姿。
“你指的是,替你杀了叶家少爷的事?”武凭勋哼笑,“杀了他倒不难。只是你拿什么做交换?”
屋里这下只有阮逐舟一个人站着。青年垂眸看着地面。
他语气倒不卑不亢:“等价交换,自然是要拿您看得上的东西来,我们合作才愉快。”
男人笑了:“你一个卖笑卖艺的乐伎,居然也能说出等价交换这四个字来。还真叫人稀奇。”
阮逐舟仍没有任何附和的笑,嘴角动都不动一下。
他等这位望江会的老大笑完,垂着眼继续道:
“如今不仅沪城,整个华国的水路都被洋人辖制,可叶家的生意依然门路通顺,经久不衰。叶家上上下下打点了哪些人,易了何种货,又走了什么渠道,这些情报在武先生看来,算不算值钱?“
武凭勋有些意外,继而眯起眼睛。
“你倒是够恨他。这些可比一个不受宠的私生子的命重要多了。”武凭勋道。
阮逐舟终于抬起眼帘。
视线相对那一刹那,男人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上一次他见到这个不起眼的男妾时,对方惧于望江会的威名,哭哭啼啼的像个鹌鹑,远没有现下这般冷静。
青年那双黑漆漆的眸子,像两把冰水里淬过的刀,不隐藏算计,却锋利得足够直白。
阮逐舟只看了男人一眼,便收起目光。
“不是他太重要,”阮逐舟淡然道,“而是叶家的命,和阮四自己的命都太不重要。不重要的事情,阮四一向舍得。”
*
从顶楼下来,阮逐舟并没急着出望江楼,而是在里面和几个打杂跑腿的攀谈了一会儿,又在门口找报童买了几份报纸。
出了望江楼,阮逐舟拦下一辆黄包车。
车子启动,与此同时,他听见沉寂了一上午的07号道:
[宿主,您和那些人聊天,又买报纸来看做什么?]
阮逐舟倒也不怕晕车,抖开一份报纸:“光靠你传输给我的记忆,想在这个副本中混得如鱼得水还远远不够。多储备些信息总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