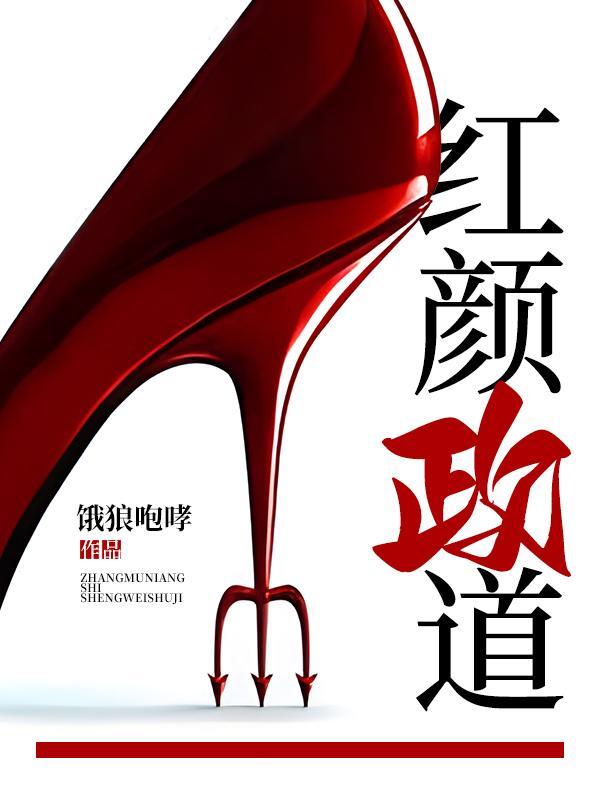三五文学>主母难为 > 第232章 文渊阁(第2页)
第232章 文渊阁(第2页)
晏菡茱笔尖一颤:“纪胤礼真去了北疆?“
“宣威将军,五品武职。“沈钧钰将凉透的茶一饮而尽,“父亲说梁御史这出戏,倒替纪家姐夫省了打点的银子。“
青瓷盏底磕在酸枝木案上,惊得窗外麻雀扑棱棱飞走。晏菡茱盯着窗纸剪影冷笑:“梁国舅这招敲山震虎,倒震出只真老虎。“
沈钧钰执扇的手顿住。暮色里妻子眉眼如画,说出的每个字却似浸过冰水:“纪胤礼若在崔帅帐下安分便罢,若真以为能凭武举虚名。“
“娘子怎知崔帅与霍将军不合?“沈钧钰忽然打断。
晏菡茱指尖抚过《北疆风物志》扉页:“上月你在书房会客,我送茶时听霍府幕僚提过两句。“她将镇纸挪开半寸,“崔帅要的是听话的刀,纪胤礼这把刀,可磨得太过锋利了。“
烛火“噼啪“爆了个灯花。沈钧钰望着妻子发间晃动的白玉簪,忽想起三朝回门时,她在永昌伯府书阁仰头找书的模样。三丈高的书架投下阴影,她踮脚抽书的动作像极了扑火的蝶。
“这些年。“他喉结滚动,“那些兵法权谋的书,你究竟看了多少?“
晏菡茱蘸墨的手悬在半空。砚台里映着窗外弦月,恍如那年趴在私塾窗根下的夜晚。老秀才戒尺敲窗的声响,与此刻更鼓声重叠。
“永昌伯府藏书三百六十二卷,百家书坊租过七百五十三册。“她笔尖划过宣纸,“放羊时偷听《战国策》,放牛时默背《六韬》,后来。“
沈钧钰突然握住她执笔的手。墨迹在“蝗“字上拖出长痕,像极了北疆告急的狼烟。
“后来怎样?“
“后来发现书里的计策都是死的。“晏菡茱抽回手,“就像纪胤礼背熟《孙子兵法》,却看不出梁国舅要的不是弹劾,是杀鸡儆猴。“
夜风卷着桂花香涌进来,沈钧钰想起今晨纪胤礼离京时的场景。玄甲映着朝阳,马上青年意气风发,全然不知崔帅军帐中等着他的,是霍家军埋了十年的暗桩。
“父亲说。“
“父亲想用纪胤礼试崔帅的刀。“晏菡茱突然截住话头,“但父亲更想试的,是陛下对霍家军的态度。“
更鼓敲过三响,袁嬷嬷添灯时见世子夫妇对坐无言。案头烛泪堆成小山,映着《齐民要术》手稿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岭南多瘴气,当以艾草熏屋“、“蝗虫畏火,可设火沟阻之“。
五更鸡鸣时,晏菡茱忽然搁笔:“梁国舅不会罢休。“
“北疆天高路远。“
“正因天高路远。“她将誊好的书稿塞进沈钧钰怀中,“崔帅若在军粮上做手脚,十个纪胤礼也不够填坑。“
沈钧钰摸着尚带余温的纸页,想起她及笄那年。永昌伯府后院,少女蜷在柴堆旁就着月光翻《盐铁论》,冻红的指尖在“平准均输“四字上反复描画。
晨光染白窗纸时,八百里加急冲进皇城。北疆战报与霍老将军的辞呈同时呈上御案,景仁帝朱笔悬在“准“字上,墨汁滴落染污了“纪胤礼阵前失仪“六字。
此刻北狄大营,纪胤礼正擦拭染血的佩剑。亲卫捧着崔帅手令进来:“将军,明日诱敌。“
“告诉崔世忠。“纪胤礼将剑插回鞘中,“我要霍家军旧部打头阵。“
帐外北风呼啸,卷走他未尽之言。三百里外驿站,梁国舅门客将密信塞进信鸽脚环,绢帛上“借狄人刀“四字被晨曦照得发亮。
惊鸿院内,晏菡茱突然惊醒。梦中血染黄沙的场景挥之不去,她攥紧沈钧钰的衣袖:“快让父亲提醒霍老将军。“
话音未落,宫钟撞破黎明。
沈钧钰望着晏菡茱踮脚取书的背影。她发间银簪勾住《农政全书》的函套,青丝散落几缕在泛黄纸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