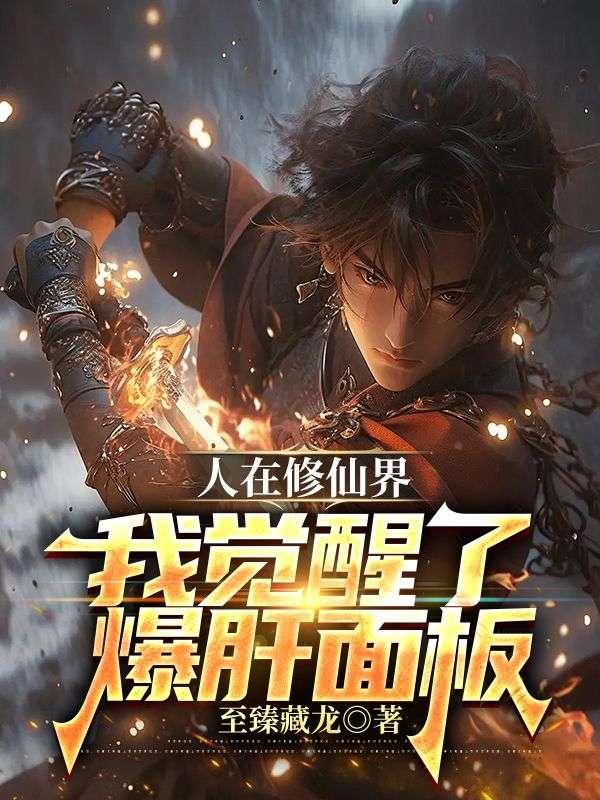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女主叫陈杳的 > 第七章(第1页)
第七章(第1页)
雨越下越大,丝毫没有转晴的意思。
梁昼沉莫名想起陈杳集训时,成宿成宿地练舞,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她总是佯装轻松,陪他出去吃饭。
后来也是一个阴雨天,陈父陈母忙于工作,托他去家里照看害怕打雷的陈杳。
他推开门,就听见像刚出生的小猫似的哼唧哼唧直喊痛的动静。
这才知道,天潮凉的时候,她会痛的睡不着觉,会把自己胳膊咬的全是血印儿。
可她。。。。。。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不害怕打雷,又有多久没和他抱怨过关节痛了。
一时怔然。
陈杳变了太多。
梁昼沉将车停到路边,忍不住揉了两下鼻梁。
副驾驶的林昭昭还没过那股兴奋劲儿,“哗啦啦”地翻着合同,指尖点着条款问他:
“昼沉哥哥,你说这块儿种丁香还是槐花?”
他没听,掀起眼皮扫了眼,当林昭昭又在说些没什么用的,“嗯”了一声,突然道:“你去打个车。”
林昭昭不明所以:
“那你呢。”
他盯着窗外暴雨,喉结滚动:
“我想一个人待着。”
林昭昭还要再说什么,梁昼沉失了耐心,干脆直接从兜里摸出张黑卡。
“乖。”
三十分钟后,陈氏集团公司楼下。
他看着空无一人的门口,突然猛打方向盘调头。
“陈杳,你他妈真行。”
梁昼沉用力锤了下方向盘,车在会所前停下时,轮胎和地面摩擦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云水间是沈迴开的,他们几个身份不方便,来自己人开的地方敞开了玩儿也放心。
说起来,他和林昭昭的第一次还在这儿。
当时他快七天没合眼,就为了在陈杳生日零点前从国外赶回家。
他在客厅里枯坐了一夜,手机屏幕也亮了一夜。
陈杳发来的消息都快被他盯烂了。
她说她在家,她已经睡下了。
可直到天将将亮,他才等到带着一身酒气回家的她。
陈杳面色酡红,连胸贴掉了一个都浑然不觉,进门就一头栽在沙发上。
天知道他当时有多想一盆冰水将人浇醒,可他到底没舍得,只将所有怒火都发泄到和她有一分相似的林昭昭身上。
看梁昼沉拿着酒进来,沈迴抬头就骂:“你他妈新婚前夕跑来我这儿发什么疯?”
他没吭声,一杯接一杯地灌酒,眼底沉着阴郁的暗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