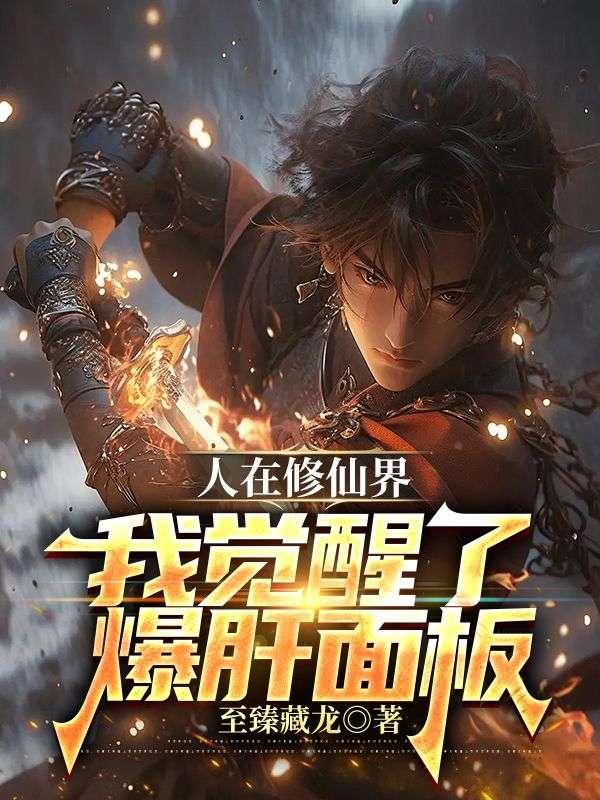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作者我有龅牙 > 第 11 章(第2页)
第 11 章(第2页)
他挤眉弄眼,急急往旁边一指。裴同衣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一缟素妇人拿布垫了些女子饰物,簪钗做工虽称不上上乘,但先前明显是被人用心收存起来的。
裴同衣望着那道远去的身影,正迟疑间,摊主又是一拍掌,“她走不远,来得及!”
*
夜渐深,街头行人愈疏。
身侧早已没了骊马温热的鼻息,但观弥料想裴同衣不会让她脱离他的视线,说不准正在某处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仍是只敢在摊前停留。
糖没买到,也没碰上什么线人,但她给城里九成的摊贩都留下了印象。
不知不觉中走至一处府邸前,观弥望着上头的“陆”字,停下来揉了揉发酸的腿。
元年八月,定国侯陆归明从龙平叛有功,封正二品辅国大将军;又立返北境拒十万敌军于关外,次年三月被拔擢为从一品骠骑大将军,权知容州军州事。
后梁封爵食邑虽分十四等,却是虚数,像陆氏这样非宗室而食实封者极少。
如今岐北三州,陆澄在易州,陆归明在容州,芫州的知州虽是朝廷送来的官,但一逢战乱还是要仰仗陆氏统协三州,多年下来,形同虚设,顶多起个通判的作用。
这处别府的大门紧闭,槛前积雪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却不像有人长居的样子。
观弥回过神张望一番,丝毫不见裴同衣的影子。她叹了口气,迈开酸痛的腿往松角巷的方向走,有些想念骊马。
*
门前竟悬了两盏小小的油灯。支摘窗上,有一道朦胧的人影。
裴同衣已在屋内静等了许久,听见声响,紧蜷的手终于放松下来,将面前一物掀开。
他赌赢了。
这么好的机会,她没有跑,是不是说明她不是细作?
观弥甫一入屋,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炉子早被暖好,一尘不染的案头上搁着个包袱。
裴同衣磨磨蹭蹭地解开,“屋里有热水。”
包袱里是几件干净的衣裳。
观弥求之不得,一番洗沐更衣后,拢着濡湿的青丝步至外间。她四处寻发绳不得,无意间发现半截发绳正被裴同衣捏在手里。
“断了。”
“我看看。”观弥放下头发,扯过发绳。
被自己掐断的发绳从指尖溜走,裴同衣看着她专心致志地将两头重新绑在一起,一时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将怀里的发簪拿出来。
“今日,”他清清嗓子,“在街上可还尽兴?”
“嗯。”
“那……”他小心地看着她身上银粉的旋袄和珠子褐的褶裙,“这衣裳可还合身?”
观弥穿惯了青蓝素净之色,头回着粉,称不上喜欢,但大致上是合身的,便点了点头。
裴同衣的心稍微落了下来。
二人静候着这一盏沸了又冷的茶汤再次热起来,细小的泡沫噼啪冒出,观弥推开支摘窗,清亮的乌瞳映着不知何时开始下落的雪。
冷风与暖意交织,裴同衣胸腔里两股情绪又重新扭打在一处。
观弥喃喃道:“瑞雪兆丰年。”
一片雪飘入屋,落在她发间,亮得刺眼,也湮灭得迅速。
裴同衣不受控地起身,抬臂,将一支素簪轻轻插入乌髻。
观弥避之不及,抓着案角,身子微僵。
“将军何意?”
“先前种种,是我不对,”裴同衣垂眸,“今日带的钱不多,这支素簪便当是……”
他声音低了下去,“给你赔不是了,秦筝。”
秦筝。
观弥顿时明白了今日裴同衣的反常缘何——她获得了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