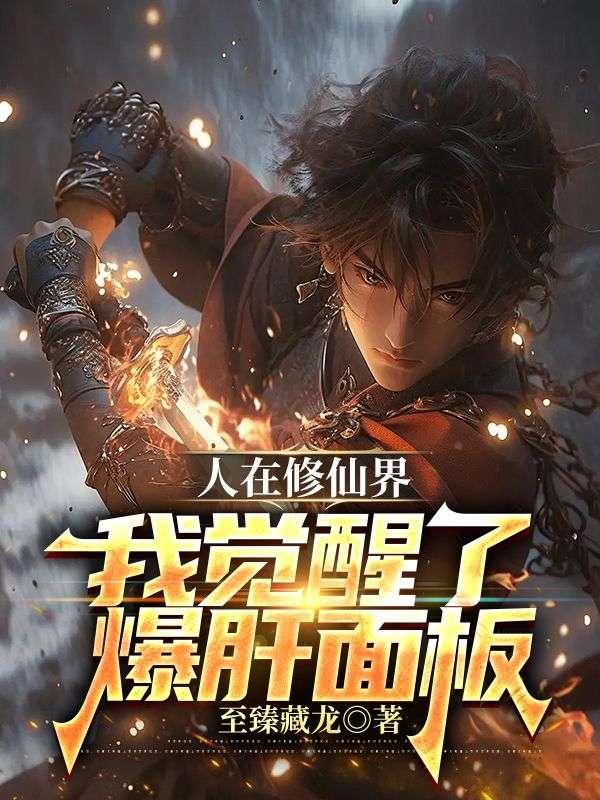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给死对头备注什么好? > 第 10 章(第1页)
第 10 章(第1页)
耳尖的红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过江荣脖颈。
“柳姑娘,”他咬着后槽牙挤出几个字,“松手。”
柳昭虞慌忙抽手时,却瞥见他仓促地将外袍下摆往腿间一扯,似是在遮掩什么。
车内气氛莫名尴尬,两人凝固在檀木坐榻的两端,一个偏头装作凝视街市,一个指尖无意识地拨弄着衣裳,就是不愿与对方对视。
索性马车很快便休整上路——原来方才行进时,轮子不幸陷入大坑,险些侧翻,这才慌忙停下。
马蹄嘚嘚敲击着地面,眼见二人的膝头愈发靠近,江荣不着痕迹般用右膝拼命抵住柳昭虞身下的木椅,双手因用力后撑而青筋凸起。
江荣整个上身不自然地侧弓着,尽管脖颈渗出一层细汗,仍保持着这个姿势,似是与柳昭虞碰一下便会当场香消玉殒。
柳昭虞平日混迹市井,难免听过不少男女之间的事情,若说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她也未免太愚钝。
看了看眼前耳尖泛红的江荣,又想起方才他在谢家伸手却不扶自己的模样,心下更是有意逗逗他。
马车又一次颠簸,柳昭虞顺势前倾,杏色衣襟堪堪擦过江荣膝头,见他拼命绷紧腿后撤的狼狈模样,柳昭虞闷笑一声,笑眼弯弯地盯着他。
“叶公子好生奇怪,平日做事一脸从容,怎得今日摸一下就红成了关公?”
面具下那双眼睛霍然瞪大,一双眸子里满是震惊地瞪着柳昭虞。
这人是在调戏他?!江荣感觉一口气堵在胸口上,差点没让他撅过去。
“停车!”
江荣猛然起身,还没待车夫掀起帘子,就一把撇开车帘一跃而下。
下次再同这人坐马车他便是狗!
三日后。
晨光还未穿透纱窗,药铺门前的小轿便已络绎不绝。
余光瞥见炉上的药罐沸溢,柳昭虞急急抽了湿布垫手去掀盖,却被烫得指尖发红,尚来不及管痛得发麻的手指,又蹲身去捡被孩童打翻在地的山楂。
今日柳昭虞本是来找王氏询问父母之事,结果一进到铺子里便忙得不可开交。
这城中女眷们自从得知京城出了位官家钦赐牌匾的女医后,天不亮便纷纷来寻诊,于是她刚进门就被谢婧瑶拉来打杂。
也不能怪她们热情,往日碍于男女大防,寻常医馆的郎中们为她们看病时,都只能隔着纱帐望闻问切,又岂能精确,于是小病一拖再拖。
可如今不仅问诊时不必设帷障,这女医更是专通妇人诸症,一手针灸之术连宫里的太医都比不上,得了消息自是满京城女子都来了。
手中的木杵撞在石块上发出闷声,柳昭虞边碾药,边用余光瞄了眼一旁抓药的王氏。
见草药磨得差不多,柳昭虞拿着药粉放到王氏跟前,看大家没往这边留意,便向王氏开口道。
“谢姑娘这番当真不易。”
她没直接开口问起父母,而是先从谢姑娘入手。
“是啊,可世上又有多少女子能有这般运气。”王氏目光温和地看着一旁的女儿,却又思及什么,略带几分自嘲地笑了笑。
柳昭虞眼神轻轻一凝,若有所思地试探道:“夫人是指……你与谢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