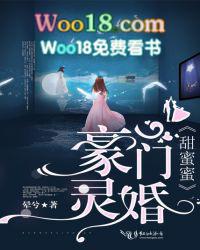三五文学>霍家养女的 > 请神送祟(第1页)
请神送祟(第1页)
剿匪那几年,曾怀义是县令跟前的红人,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左右逢源,风头无两。
可那时的他,毕竟太年轻,不知道有句话叫,“功成之日,便是鸟尽弓藏之时”。
那十数股匪盗里,得以搭上这趟官船的只有他和另两人。事成后,县令称,若在原县呆下去,身份难保不暴露,只怕对他们日后前程有碍,转将他们安置去了他县,托付给同榜同年的至交,定会好生重用。
三人踌躇满志地去了,满以为可以自此青云直上,不料却是悬崖直坠。
苦的、累的,还有那送命的,都有他们。举凡能立功、能露脸的,就没他们的份儿了。
这般遭遇在衙门里原是寻常,无根无基的人,从来都是干活的“命”,没有升迁的“运”。
可这三人,谁家往上数八辈子,也没出过吃公家饭的,哪里懂这其中门道。
在占山为王的匪盗里,这三人都算有心眼的,可到了衙门里,却都成了直肠子莽汉。他们在此是两眼一抹黑,心眼不够用,就连最擅长的用拳脚说话,在这儿也说不上话了。
做惯了山匪,哪习惯得了衙门里的处处拘束。当惯了头头的,又哪受得了明里暗里的排挤欺压,做事、论功和行赏的不透明不公正。
不多久,三人里便走了一个,忽一日又送命了一个。几个月下来,就只剩了曾怀义一个。
这日,那兄弟的家人来扶灵回乡,曾怀义送出城去,转头回来,进了城门,只觉饥肠辘辘,想就近找个地方吃饭。
一抬眼,迎面走来个熟面孔,正是贩货到此的樊仲荣。
只数月不见,樊仲荣见他仿佛变了个人,没了先时的风发意气,灰头丧气,一脸郁郁。
他也不点破,仍亲热地拉着曾怀义找了个酒馆坐下,等好菜好酒上来,吃饱喝足了,才闲话着旁敲侧击了起来。
他乡遇故交本就亲热。曾怀义憋屈已久,烈酒下了肚,这几月以来的种种郁愤便都浮了上来,成了下酒菜。
樊仲荣听完,也不宽慰,只又陪了几杯酒,才故弄玄虚地道:“明日午时,咱们还在这里见,到时我有件事要拜托怀义兄,万望不要推脱。”
什么事非得等到明日再说?
曾怀义不由纳罕,可那樊仲荣绝口不提,一味劝他喝酒吃肉,他也就不强问了。
第二日午时,曾怀义依言来了,都喝完了一坛酒,却还不见人。他下午还要当差,便嘱咐小二替他带句话,起身就要走。结果,转头就见樊仲荣拿了个不轻的包袱,喘着粗气,匆匆走进店来。
樊仲荣抬手往下一按,示意他坐下,走上来,也顾不上擦汗,把包袱放桌上,往曾怀义面前一推:“这一包金银,合银三百两,可解兄之困局。”
“三百两?!”洗墨惊叫了一声出来。
高升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眼里分明在说他没见过世面。
连周冶听了也心惊,这可是县令三四年的俸禄,足够在京城买座过得去的宅子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以当时的曾樊二人来说,绝对是笔巨款。
当年的曾怀义自然更是震惊,既震惊于他拿这么大笔钱给自己,也不明白这钱如何能解他的困局。
曾怀义将银子推了回去:“我虽诉苦,却不曾哭穷,仲荣老弟这是为何?”
***
樊仲荣笑笑,又推了过去:“这不是给你用的,是要你拿去上下打点的。”
曾怀义无奈笑笑,将银子推了回去:“我是前途无望了。何必浪费这些钱,填了那些人的口袋?你今日给了,就不怕我今生都还不上?”
这酒馆临河,樊仲荣往窗外看去,见对岸有人在河边焚香烧纸。
他一笑,指着窗外道:“怀义兄,你说世人撞邪送祟的时候,为何都要焚香烧纸?”
曾怀义不知他是何意:“这请神送祟。。。。。。自古以来不都这样?”
樊仲荣见他酒碗空了,先给他满上,才道:“这请神送祟,常常是在水边、十字路口焚香烧纸,送上买路钱,将它们都请上路,好走,勿扰。这买路钱,买的就是个不生事,不挡道。”
曾怀义听着有点儿意思了,端起碗来,朝他一举。
樊仲荣抬起碗,跟他轻轻一碰:“这搬家到了新地方,是不是先要向左右邻里送点小礼,结个善缘,以便日后相互帮衬?小门小户里,逢年过节是不是也要往来迎送一番?这当家理事尚且要人情往来,做官如何不要?”
曾怀义心道,果然如此。民间很多习俗,世人虽照做,却从不曾细想。如今想来,那如何不是先人代代相传的智慧?
可叹他孤儿寡母,流落千里到此,活下来都不易,哪里还有余力去人情往来?他长到如今,一无习俗可遵,二无家学可承,全靠自己看别人做一样,跟着学一样。
曾怀义转而拿起酒壶,去给樊仲荣添。
樊仲荣客气了一下,双手捧着碗去接:“你便是进了庙,向那普度众生的神佛许个愿,也要先上香叩头,后还得添灯还愿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