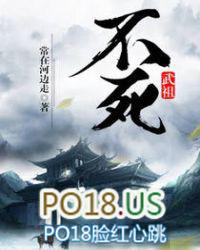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你是我年少求剑时刻的舟什么意思 > 第 4 章(第3页)
第 4 章(第3页)
毕竟是在在自家公司靠关系混饭吃,温辞搞得有模有样,她也得混的像样点。
晚上七点,她准时收工,坐地铁回家。手机在包里震了几下,是几个同事在群里发笑话,她懒得回,一整天累的她已经没有力气,等到站后才掏出手机。
出了地铁站天已经暗下来了,她在便利店买了杯热牛奶,边走边喝,走到小区门口时,一阵风吹过,她下意识拉紧风衣领口。
夜风吹在脸上,有些凉。
—
城西另一头,谢丞礼提前回了家,晚饭没吃多少,只喝了几口海鲜粥,吃了半份青菜。
洗澡前他按惯例做了一组滑轮训练,但因为肩关节不太舒服,做到一半就放了下来。他把自己转移到浴室的洗澡椅上时,动作比平时慢了不少,肩膀一阵一阵地抽痛,右臂没办法用力支撑,差点在瓷砖上磕到手肘。
他愣了一下,停在那里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调整了姿势,把轮椅移回扶手位置,用毛巾垫着擦干身体。
动作熟练,但每一步都沉默。出了浴室后没开客厅大灯,只是坐在窗边一盏落地灯下,把白天的那份设计稿又拿出来翻了一遍。
温尔的字迹很好认,清爽娟秀的,但每一个笔画都写得有力。他翻到最后一页,是手绘的走秀动线草图。她用蓝色的墨水笔在下方写了几行附注说明,还贴了一张回收布料的样品卡。
那张卡纸下方,被她按了个角,边缘有点翘起。谢丞礼伸手摸了一下,指腹碰到那处卷边,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那一角很可爱。想起很多年前,温尔还在上中学,选修了服装设计,第一次做作业时,拉着他说:“你坐着别动,我想看袖子从你手臂垂下来的角度。”
那时候她才十七岁,连尺都不太会握,画草图也总是歪的。
他坐在阳台晒太阳,她靠在他的膝盖边上画,头发不时蹭到他手背,他没敢动,就安安静静地看着她画。
她一边画还一边嘟囔:“你不要一动不动,我又不是给你画肖像。”
他想说点什么,但没敢说。那会儿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喜欢她了。只是他的年纪太大,两人身份太近,他不知道能怎么表达,只能小心地维持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这个角色。
后来出事以后,他也不打算敢了
身下的轮椅和无人看见的狼藉,像一堵墙,把很多话都挡在了心里。
——
晚上十点,温尔坐在沙发上改一份剪裁稿。她看着屏幕上衣片拆解图时,不自觉地想到白天谢丞礼坐在那里的样子。
他还是那个沉静的样子。而且多了点她看不太懂的东西。她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但她希望以后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他了。不是为了“让他看到自己努力”,也不是为了“重新靠近”。她是真的只想做自己了。
温尔点开新建文件,把一组袖山变化做成独立文件,给样衣组传过去,又附了一行说明:
“该款适用于坐姿状态下肩臂活动,袖口顺延平放,不堆积。”
发完后她关了电脑,去洗了个热水澡。吹干头发,坐在床边喝水时,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很久以前,她曾给谢丞礼写过一封信,放在他的车里副驾驶储物箱里。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只写了一句话:
“我不是小孩子了,不要再把我挡在外面。
那封信后来有没有被他看到,她一直不知道。但她已经不想再问了。
——
谢丞礼夜里又醒了一次。他不是第一次失眠,但是自从温尔回来后,失眠格外频繁。
他拉着床边的栏杆翻了个身,听到紧贴在床边的轮椅轻轻晃了一下,碰撞的声音很轻,却打断了别墅里整晚的沉默。
他盯着天花板发了很久的呆。脑海里反复响着白天她走出会议室时,那个干净利落的背影。
他想着,伸出手缓缓从自己的肋骨处往下摸,从隐约感受到触摸,到像在摸别人的身体。
过去的这几年,在他一动不能动的时候,她不是原地等着。
她一直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