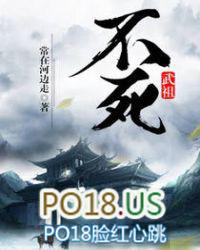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东宫笼中雀笔趣阁免费阅读全文最新章节更新 > 第79章 他死了你凭什么还活着(第1页)
第79章 他死了你凭什么还活着(第1页)
大雪纷飞,愁云密布。
北都皇宫之中人心惶惶。
那日下午南月苑中发生的事情,早已如一阵风般顷刻传遍了宫内宫外。
慈宁宫第一时间派了人来,却被玄甲卫的铁刃刀锋尽数挡在了南月苑外,即便太后懿旨也传不进去,也就更别说其他人的耳目。
之后帝王接连罢朝三日,同一时间从南月苑源源不断抬出的宫婢太监的血淋尸首,令人骇然失魂。
自出生起,便得到帝王无理由偏爱的小太子以及生母北护王妃,亦一开始被监禁起来,非帝王圣旨,无人知其生死。
帝王一怒,伏尸百万。
不少年龄稍大的老人,又恍惚想起,似乎同样的事情,在二十多年前好像就发生过,而当初最后的结局,恐怖得没有人想再回忆第二次。
而帝王迟迟不出现,朝中早已乱作一团,最后还是元国公带一众朝臣齐齐冒雪跪在宫门之下足足一整天,这才请得帝王再度身着玄黑龙袍登上金銮殿。
可紧接着,臣子递上的时隔多日的第一道请奏,便是请帝王赐死那胆敢伤及龙体的君子相遗孀,帝王却怒而拔金剑,直接在金殿上砍下了那进谏大臣的头颅,丢下剑,站在血泊中,怒形于色放言道,倘若日后还有人上谏要将那人赐死,便是公然要与他为敌!
直到有人突然来到帝王身边,低声耳语数句,帝王顷刻扭身便丢下所有朝臣离开。
余下所有人心有余悸,突然听到殿中惊呼一声,原来年事已高元国公突然仰面直挺挺倒下,被送回国公府后,很快就传出中风的消息。
而匆匆从前朝赶回南月苑的沈长冀一跨进殿门,殿中乌压压的御医便立即缩头,赶紧退至两侧,让帝王穿过,大步来到床边,正好看到御医署首席李文颀将床上正给昏迷不醒的人脖子上抽出最后一根银针。
看到床上人的脸色比自己先前离开时要差上不少,沈长冀心都停了几瞬,脱口便问:“发生什么了?”
李文颀额上一层汗,道:“臣启奏陛下,南公子方才脉象骤乱,气若悬丝,险入膏肓之境,虽然臣已急施金针渡穴,并用参汤吊命,暂时稳得形骸,但南公子脉象涣散如游丝,神光游离若残烛,全因心火尽灭,神志自绝,臣虽竭力维系一线生机,然生死之机终系于病者一念之间,若南公子七日内仍无求生之志,恐……”
沈长冀逼问:“恐什么?”
李文颀咬咬牙:“恐大罗金丹亦难回天矣……”
沈长冀瞬间如遭重锤,倘若不是惜月眼疾手快扶住,他怕是会再顾不上什么帝王之仪而跌倒。
他强撑着放下狠话:“朕命你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回他,否则,你们御医署便统统给他陪葬!”
李文颀一众御医顿时纷纷跪下,“陛下息怒——”
中庸每日要喝不下三碗汤药,沈长冀把人抱在怀中,惜月舀一勺稠苦的药汁送到中庸嘴边,却发现中庸竟含入嘴中的汤药没有咽不下一滴到腹中,尽数从嘴角流出。
惜月听到李文颀悲声道:“南公子气血枯槁,又拒饮拒食,这是在自绝生机啊!”
小年与小齐子听了这话,立马相互抱着哭泣起来。
惜月急得不行,却也没打算就此放弃,刚想问有何方法能让中庸喝药,却猛地听到殿中齐齐一阵惊呼声,望见周围所有人瞪大的眼,她立马朝床榻上看去,却震惊地看到已经含下一大口药的沈长冀,正嘴对嘴吻住中庸,强迫地把汤药灌入昏迷不醒的中庸口中,有棕褐色的汤汁蜿蜒从中庸嘴角流出,甚至沿着脖颈没入素色衣领之中。
但马上所有人骤然回过神来,纷纷背过身,只能听到殿中响起轻微的吞咽水声。
最后,虽然有不少汤药浪费,可比之原本那大一碗汤药,绝大多数都还是进了中庸肚中。
之后的几天,沈长冀几乎是寸步不离床上中庸半步,每一碗汤药都是他口对口地逼中庸喝下。
帝王几乎不睡,时刻盯住中庸病势变化。
可即便是世间最强大的天乾,这般耗下去,精气神也肉眼可见迅速衰沉下去,可他仍旧强撑着不肯倒下,眉眼间满是怕会永失所爱的惊惧失惶。
到第七天,精神恍痛的惜月都已经报着送中庸最后一程的心态走入殿中,却看到帝王紧紧握住床上中庸的手,额头贴了上去,眼眶微红,颤抖的嘴里念念有词,卑微至极祈求道:“菩萨佛祖,倘若你们这次不带走他,长冀愿意为你们修筑万座佛庙,供奉百年香火,只求,只求你们能垂怜我这一回,不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惜月的心也痛起来,刚欲退下,却猛地瞳孔放大。
隐隐听到惜月在身后急又轻地唤了一声,沈长冀正抬起头询问,却蓦地看到一双病弱疲淡的琉璃瞳正望着自己。
沈长冀顷刻身体立住,不敢眨眼,生怕自己一眨眼,眼前的眼睛便会重新闭上。
可当他看到中庸的唇微微张开,似有话要说,沈长冀终于意识到这一切并非自己的幻觉。
以为对方是想告诉自己可能哪里不舒服,或者是别的想要的什么,沈长冀立马起身附耳去听中庸的话,“阿、阿泠,你是不是有什么要和皇——”
下一瞬,声音与男人的身体一起猛地僵在空中,整个人似掉进无底的漆黑深渊。
因为他清楚地听到中庸用极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对自己吐出的竟然是:
“他死了…你凭什么…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