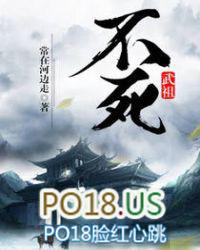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拒婚完本 > 鹤州之行(第3页)
鹤州之行(第3页)
季姰没回答,只是领着谢既走了进去。此时正值傍晚,楼中果然如季姰所说,放眼望去全是食客,楼上楼下瞧不见一个空桌子。自楼顶横梁悬下一座锦鲤灯,灯火喜庆,甚为醒目。
掌柜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一身暗红布衣,头发也用同色的布条盘住,打扮与这座称得上富丽堂皇的酒楼不太相称,但气势十足,一瞧就知道是主事之人。季姰和谢既二人长得出挑,一进门她就注意到了,将手中账本扔到一边就大步走到两人面前。
“呦呵,这不是季家丫头吗?终于有空来看看我了?”
见女子语气熟稔,谢既诧异地挑眉,没出声。
“兰姨。”
季姰露出个乖觉的笑来,同这被称为兰姨的女子攀谈片刻,而后兰姨随手招呼过来一个小厮,叫他领着二人上三楼。
两人绕过屏风,于包间中隔桌对坐之时,谢既还是有点没反应过来。季姰拿起茶壶给他倒了一杯,推到他面前:
“这儿的杨梅饮最好喝了,三师兄尝尝。”
“你认识这儿的老板?”
“算是吧,主要是我爹曾经救过她,她跟我们家也有十余年的交情了。”
“啧,差点忘了鹤州是你的地盘。”
“过奖。”
两人交谈片刻,菜就一道道的上来了。整整十二道,菜式各异,色香俱全。
“话说三师兄你辟谷了能吃多少?”
季姰突然想起这个问题,修行之人基本不吃东西,更别说油腻荤腥。
“怕什么,你吃不完就放储物囊带回去。”
谢既捏着茶杯,咂了口杨梅饮。
“好主意。”
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黑,二人酒足饭饱——应该说季姰单方面的饱了,谢既就没动过筷子,倒是喝了大半壶杨梅饮,见季姰吃差不多了,慢悠悠地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
“三师兄,这顿我请你吧,我还有钱。”
季姰把银锭推回去,却得谢既一记眼风,不敢动了。
二人沉默片刻,季姰缓过神来,扭头问他:
“所以三师兄说的惹祸就是咱们失踪?”
“差不多吧,我失踪不很要紧,你失踪天翻地覆。”
“有这么夸张?”季姰不信。
“那当然了,你可曾见过咱们宗门上下有谁敢惹大师兄的么?”
那确实好像没见过。
“大师兄给你护得密不透风,你从他眼皮子底下跑了,也就是你有这个胆量,确实令人佩服。”
谢既双手抱头往椅子上一靠,慨叹道。
“这还得多亏三师兄倾情相助。”
季姰也不太敢确定,但沈祛机明确是不太想瞧见她,就算她暂时不见一阵兴许也问题不大——说不准这都不能称之为惹祸,没人瞧见,就当是她回乡一游也不错。
“我护着你人身安全还是没问题的,大师兄充其量罚我练功面壁罢了。你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纸糊的美人灯,我还真好奇大师兄如何罚你。”
“说实话我也好奇。”
季姰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眼眶湿润。她随意往窗边一瞥,却见远处层层叠叠的楼顶上,似乎有什么黑影悄然掠过,形状不明,颇为诡异。
“三师兄,窗外那是什么?”
“什么什么。”谢既不甚在意地顺着她的目光瞧过去,神情瞬间冷凝,像是一块烧红的烙铁骤然被扔进冰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