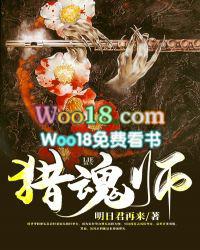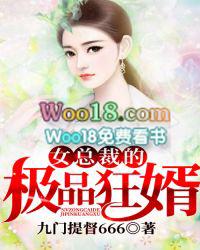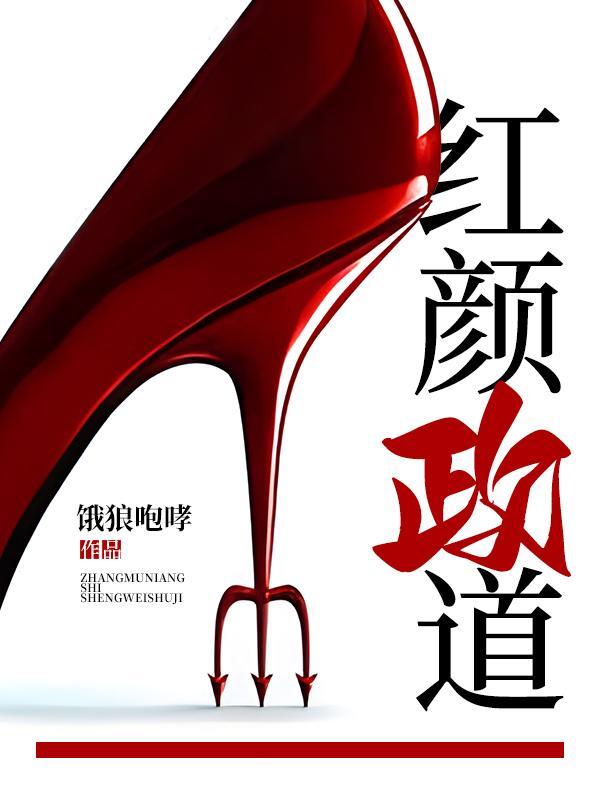三五文学>穿成七零村霸 > 编制(第1页)
编制(第1页)
几位老师对这种选拔方式很感兴趣,反正没卷到自己身上。他们讨论起来,连姜知年写来面试抽选的题目都一一看过,最后点评,很严谨,就该这样。
公社的梁书记不知为什么也来凑热闹,知道大多流程出自姜知年之手,好好夸了她一番,说她真是文武双全,武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能出题写文章,又骂陈三叔不厚道,平常没事都要吹三分,这回侄女的文章都选上人民日报了,他却悄咪咪的。
陈三叔:我不造啊?
姜知年就没想起来,当然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毕竟文章不是她主笔。村里没订报纸,她本来想等几期文章登完,等叶遥给她寄合订本,再拿给陈三叔宣讲的。
等等,人民日报?
姜知年也很错愕,梁书记看她的表情不似作假,笑着点点她:“怎么,不是你写的稿子吗?不记得了?”
她解释了一番文章和叶遥和她的关系,因为没有收到叶遥的来信,又没订报纸,所以不知道文章被转载,从书记这里得知这个消息她也很惊喜云云。
“好孩子,你们写的东西很有警示意义,有责任有担当,你叔没教错你……”
梁书记还想再夸夸她,不过看这叔侄俩都是懵懵的表情,笑笑摇着头走了,又让陈三叔回头找他取报纸。
陈三叔反应过来,重重一掌拍在她肩头,大笑着追领导去了。
姜知年还在思考叶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连编辑回信都要给她抄送一份的人,怎么会不来信呢?还是等这摊事搞完赶紧去封信问问吧。
上午考试一共考了两个小时,一点前卷子已经阅了出来,除了主观题由老师、村和公社领导评阅,文化课由姜知年带着一群不参与考试的初中生对答案打分,选出十个人进入下午的面试环节,村里的年轻人也很“争气”,有四个进了复试。
杨君梅果不其然在第一轮就被刷下去,姜知年一点都不意外,她早就看清她的学渣本质,背个课文两天都背不下来,救不了,这是真的救不了。
进面的知青有纪清瑜、李佩、邹志强,新来的卫莹,最早一批的韩其栋,还有……赵知节。姜知年看过他的答卷,卷面工整、字形圆润,主观题有理有据,连村民评价都不乏夸赞。
姜知年保留看法,后世一轮轮筛选照样筛不出人渣,反正她确信自己是个好人(大雾)。
面试的内容需要抽选题目,留半个小时备课,然后试讲,考官提问——包括一众小学生在内的考官哦。
大人做结构化面试,小孩问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还能看出面试人对学生的态度,姜知年为自己点赞,她真是个天才!
纪清瑜教案不错,但讲课方面不如李佩,卫莹比邹志强强点,讲课更生动,韩其栋是表现最好的,赵知节……姜知年表示这不赖她,她都没来得及使绊子,这货上台就磕磕巴巴的。
四个村民最后选了魏雨晴,刘朝阳堂爷爷家的孙媳妇,以及陈昼——驴蛋堂哥,这两人的表现跟卫莹差不多,但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江文斌和钱美华遗憾落选。
通知过最后的结果,又告知落选六人以后学校扩招会优先考虑他们,这场选拔便结束了。学校选址就在大队部附近,考官们去看了砌土坯的场景,说笑一阵,便各自散了。
时间已经过了五点半,姜知年看看日头觉得来不及,只能等明天再去邮局了。
晚上的饭吃得她心不在焉,她都脑补到被人贩子报复的阶段了,所以陈三叔问她什么都没注意,只“嗯嗯嗯”。睡觉前再想起来,却发现根本没有他说什么的记忆,算了,重要的事他会揪着她再说一遍的。
第二天一早,她赶着邮局刚开门就去发电报,一个字七分!计费字数十个起算!“文上报信未到出事否”九个字就七毛,这钱花得她肉痛。
更肉痛的是她发完电报邮局工作人员看了眼她的名字说有她一封信……
正是叶遥寄来的,信里说她堂弟叶邈下乡就在红卫公社,她托堂弟带了东西,一直没收到姜知年的回复,便问问她的情况,以及是不是堂弟出了事没告诉他们,希望姜知年能帮忙查问。
姜知年仔细回想这批新知青的情况,叶?那个桀骜不驯、瞪眼看人的男生好像就叫叶邈。靠,这可真是个臭弟弟!
她愤而转身,追加一封电报,“弟在本村,未找我”,又写了信解释了两份电报的原因,委婉表达她弟弟可能有点欠揍。
气冲冲回村找人,没找到,先被陈三叔揪着耳朵拉去大队。
知青陶耘是个腼腆的小男生,他父母都是省农科院的研究人员,他本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自然也对农业技术有所了解。
一早大队长就叫他到大队部,然后,姜知年久久不见人影,大队长满村找人,看着大队长火冒三丈的样子,本来有些紧张的他,神奇地放松了。
姜知年不确定这个年代有没有大棚技术,也不清楚是否能生产塑料膜。现在有了一个懂行的,他介绍现在北方地区广泛使用的是高1米,宽1。5到2米的小拱棚,大棚技术应该有,但不知道具体的。地膜覆盖种菜的技术也早就有,他记得是一位赵姓教授的研究成果。
他觉得种反季蔬菜、温室水果的想法,对柳树大队而言是个赚钱的好路子,所以在姜知年请求他帮忙联系专家时爽快同意了,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想要请假回家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