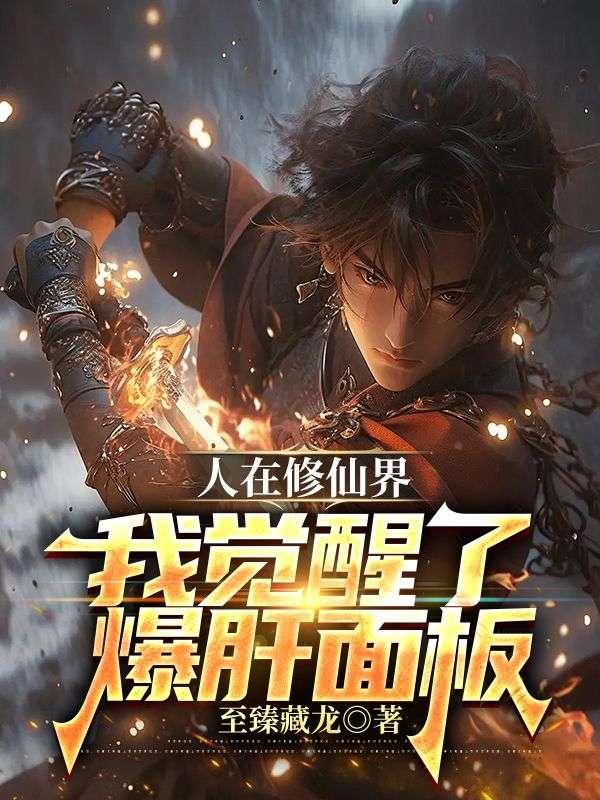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复生攻略快穿by快穿免费阅读 > 3040(第12页)
3040(第12页)
余逢春坐在中央的椅子上,周身覆盖阴影,唯有那盏烛火带着些许暖光,给拨弄烛芯的时候投下更鲜明的分界线。
囚徒看不清他的面容,只隐约感觉这次来审问的人和其他几个不一样,更冷静也更从容,拨弄烛火的模样好像是在斟酌挑选他们的命,琢磨着从哪个开始下手。
良久后,等到连呼吸都僵硬无力,余逢春才缓缓开口:
“你们偷了什么?”
“这……”
几人跪在地上面面相觑,一人率先将头用力磕在地上。
“奴才是想偷的,但没有偷到……”
余逢春眉头忽的一挑。
“没有偷到?”他重复着囚犯的话,尔后问,“那你们本来是想偷什么?”
“我们四人只是临时起意,想偷些珍奇古玩带到宫外去换一些银子,并没有具体要偷什么,大人明鉴啊!”
余逢春闻言冷笑一声,盯着眼前抖成筛子的四人。
光看他们穿的囚服,就知道邵逾白没对他们动刑,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动机在邵逾白眼里太过明显,以至于不需要逼问出什么就能直接确定答案。
但这样的无视和宽容,却让他们以为还有活的可能,以至于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沉默许久,余逢春将烛火端正放在地上,站起身来。
“知道从这里再往上一层是什么吗?”他问。
这个问题来的没头没脑,几名囚犯眼中闪过困惑,不知道余逢春想干什么。
而余逢春也没有真正期待他们的回答。
“在这层往上,有一处空间,用石板和着米浆筑成,最是坚固,人力难以摧毁。”
他弯腰熄灭烛火。
在黑暗中,恐惧放大,连平稳讲述的声音里都带着几分阴森。
“这处空间被分割成几间,每间的进出口仅有一尺,内一无床榻,二无烛台,黑暗冰冷,且因为墙极厚,所以也没有声音。”
“将犯人关进去后,守卫会关闭进出口,除了每日一餐外,不会有一丝光亮、一点声音传入,就这么长年累月地关着。”
不紧不慢的脚步声仿佛踩在人的心跳上,混着淡雅幽微的香气,每一步落地,都能让人怕得把心吐出来。
余逢春盯着犯人哆嗦的肩膀,阴恻恻地笑了一下。
“陛下仁慈,不愿对你们动刑,但并不是非得见血才能得到实话,若是将你们分开放进去,不出半月,死的死疯的疯,还怕得不到实话吗?”
戏谑的声音中藏着浓厚的兴趣,仿佛这个儒雅淡定的大人真觉得这是件多有意思的事。
果然能被派来审讯的,都不是什么正常人。
四名囚犯跪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几日的囚禁已经把他们的所有胆识全部磨灭,唯一的一点侥幸也被余逢春的话吓得再也冒不出头。
见他们已经被骇到,余逢春趁热打铁,柔声喊:“陛下已经派人去了你们家乡,将你们的父母亲眷接来保护,若你们还不知好歹,辜负陛下恩德,那就只能——来人!”
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
种种逼迫下,囚犯心理防线被压到极致,终于不可控制地崩碎开,一名囚犯哆嗦着开口:
“——大人且慢!!”
余逢春一转身,挥手让进来的守卫退下:“愿意说了?”
“是……是!”
囚犯跪在地上,声音沙哑,饱含恐惧,已看不出一刻钟前的强装镇定。
“启禀大人,我们确实有要偷的东西!”
“是什么?”
囚犯忽然哑下去:“这……”
这时,另一名跪在左边的囚犯大声接道:“大人恕罪,我们真的没有见到那两样东西,只是听人说,是兵符,和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