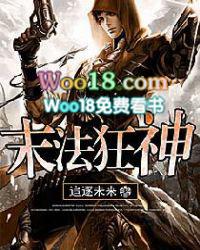三五文学>内卷后我咸鱼了 > 第四十三章 登基第三十五天(第1页)
第四十三章 登基第三十五天(第1页)
邵吏的意思模糊,若是不了解官场潜规则的,不一定会清楚他在说什么。
看似句句控诉,却连一点有用的话都没说——直到如今他还时刻记着,万万不能说出宝鸡县如此的原因。
邵吏在此处苦熬了十多年,此次春汛,他算是看清了自己在上峰眼中的位置:不论如何努力,都只是他们手下的一条狗罢了,只是和真正的牲畜不同,心情好了他们或许会给狗一碗肉汤,而他什么都没有。
“你若心中有怨,大可直言。”贺隋光冷静地看向对方,“或者,你在陛下面前开口。”
“你不信我,总该信陛下。陛下登基以来,所行桩桩件件,皆是有利于百姓之事,你应该能看到。
贺隋光仍是心中有怨气,说话也不大好听:“陛下不会对任何一件不平之事置之不理。”
外面的灾民还需要看顾,贺隋光没时间再和这人废话,只叫小吏将他捆了,先塞在县衙不用的房间里,等待此处的事处理好后,再押送去燕都。
——宝鸡县管成这样,不论背后有什么原因,这位县令都要担首责。
县丞小心翼翼地从内间出来,给燕都的天官行礼,他看起来与邵吏也差不到哪去,面色沧桑,看不出真实年龄:“下官见过寺正。”
“不必,你先与我说说,宝鸡县现在是什么情况?”
贺隋光帮助处理过不少县的灾后重建事务,已然得心应手。
“如寺正所见,宝鸡县内早已没有存粮,上下人口不足七万,每年纳税不过二万零八十三石,乃是下县中的下县。”县丞小心翼翼地介绍,“如今大人带了朝廷的赈灾粮下来,这群人便有了活路,能够支撑着补青苗,或许能补上今年税收……”
“不必,陛下说了,凡受灾县,皆今年免税。”贺隋光道。
“好好好!”县丞的脸上露出一点笑意,一连说了三个好字,简直喜极而泣,“这下县内的百姓,总算能活下去大半了。”
“再有,不日陛下会送来另一种不同的作物,只是你们要记住,这些良种没有经过特殊培育,三年后会逐渐失效,所以一定不能只种植良种,稻谷也要种。”
县丞的眼睛里都有了光,殷勤地奉承几句:“大人所说,臣一定转达下去。想必清楚,这税收也是收粮食,而不是那什么良种嘛!”
有了这匹救济粮,再加上未来的良种,宝鸡县的情况肉眼可见便能好起来。
“再有,还会送来一些新型材料,用以巩固堤坝。朝中又在征集治水之策,你们放心,朝中会尽量减少汛灾之事。”
县丞欸了几声,一拍脑袋,道:“大人,邵县令善治水啊!他日前提出的治水良策,听说呈上去被陛下夸赞了!”
这些贺隋光倒是不大了解,只依稀听陛下提过一嘴,有人呈上的奏疏很得他心意。
那似乎……是知府的奏疏?
贺隋光直觉其中有异,不着声色地追问:“是吗?不过朝中治水能人甚多,待我禀明陛下后再做定夺。”
县丞担忧和自己共事许久的县令去了燕都,就直接入狱,再也没有出来的可能,于是现在不遗余力地介绍:“大人有所不知,十多年前,宝鸡县的样子更凄惨些,汛期时,几乎所有田地都被淹没,人口也只有区区五万。如今、如今已改善许多了!”
这话若是真的,那邵吏也不像个没能力管理的人。
怎么偏偏弄成这副德行?
贺隋光心中犹疑。
接下来的几日,他都在配合县丞完成救助之事,二人配合得不错,很快,县中秩序恢复了一开始的井井有条。
当工部的水泥运过来时,已经和其他县相差无几,只是灾民恢复、以及田亩重整还需要时间。
“寺正,这是最后一批水泥,应该正好够这边的堤坝修理。”运送的小吏气喘吁吁,这些东西死沉,运送过来耗费了不少时间,“水泥窑选址在前边的县,去干活的百姓都算徭役,每日发十五个铜板。”
县丞在一旁听着,知道这就是寺正口中说的,陛下遣人送来的新材料?
只是为何将其称为“水泥”?
于是问道:“敢问各位,这水泥又是何物?又该如何使用?”
第一次听到“水泥”这个名字,不少人觉得古怪,又是水又是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才清楚,是加水后塑性、使用的“泥土”,知道这是陛下取的名字后,果真不同凡响。
那小吏介绍几句,末了还说:“别看这名字古怪,实际上用处真不少,陛下还说,不同县之间连通的路,也可以用这个修一修,让百姓出行更方便,某些村人迹罕至,也不至于困死在里面。若县中有需要今年服役的,也可去水泥窑干活,陛下说了,一人一天有十五文钱。”
这点钱不多,但却是意外之喜。
要知道,除却正税之外,百姓每年还要服徭役,包括力役、军役和杂役等,这些徭役都是无偿,还只限定壮劳力。但凡服徭役的家庭,都怨声载道,影响这一年的收成。
水泥窑却一反常态,不仅算正役,还给钱,这对刚刚从汛灾中恢复的百姓来说,可谓是及时雨。
再者,为了不影响后续的收成,水泥窑只暂开着一段时间,先将各处堤坝加固。后续修路所使用的水泥则是慢慢烧制,多在农闲时加快进度。
听完这些后,县丞激动地诶了一声,向着燕都的方向行了一礼:“陛下仁心。”
别的县他不清楚,但是宝鸡县的劳力不少,眼下田被淹了,想要恢复还得一段时间,正好能去水泥窑。不如说,这项规定,对越贫困、下田越多的县而言,好处要多于上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