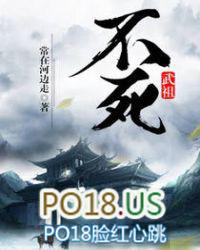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是一本百科全书 > 第515章 不辜负任何百姓(第1页)
第515章 不辜负任何百姓(第1页)
夜风卷着良乡郊外的雪,吹进京师的窗棂。
魏昶君披着一件洗得白的粗布袍子,手里提笔,在麻纸上勾画着密密麻麻的物资清单。
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满了各种物资,黄公辅举着油灯凑近,灯芯爆出个灯花,在每人加配棉鞋一双的字样上投下影子。
“里长,这。。。。。。”
黄公辅泛白的鬓间,生出几分忐忑。
如今他已经主政红袍军民部良久,但如今竟迟疑了许多。
“光是冬被就用去库房新弹的棉花逾数十万斤,再加上这些。。。。。。”
他手指点在桐油防水帐篷,烙饼,水壶上。
“他们到底也只是一群投降的边军,如此是不是有些过了?”
魏昶君头也不抬,笔尖在纸上重重一顿。
“过?哪里过?”
既然开口了,黄公辅也没有继续藏着掖着。
“每人两套棉袄、三双布袜、一条羊毛毯子,还有。。。。。。”
黄公辅叹息一声。
“行军被褥里塞的是新弹的棉花,不是芦花!这。。。。。。这比京营将领的铺盖都厚实!”
魏昶君冷笑一声,似乎又看到巨鹿鏖战时溃散的京营将领。
“京营?京营的兵冻死在辽东雪地里的时候,他们的将军在暖阁里喝参汤!”
“吴三桂之流的确欺压过百姓,但那些边军将士在启蒙师的教导下的已有所改变,你们不会看不到,这些儿郎们去西南是要趟瘴气的,万历年间征播州,冻死的兵比战死的还多。”
黄公辅愣住,旋即苦笑。
他似乎有些明白里长究竟在想什么了。
自家这位里长,永远将这些最底层受苦之人,看的比自己还重。
有时候他甚至感觉,这整整数年光景,里长从未改变过。
他依旧是那个一心想将所有百姓托举起来,让他们挺直了脊梁做人的普通人。
窗外传来三更梆子声。
魏昶君起身推开格窗,夜风裹着良乡郊外的泥土味涌进来。
明明相隔甚远,他竟然仿佛能看到远处营地的篝火如散落的星辰。
“老黄啊。”
魏昶君忽然放软了声音,指节敲着窗棂,这是他头一次这般称呼这位红袍军的大管家。
如今他转头,目光落在这个须皆白的老者身上。
数年时光,他看起来已苍老了不少。
黄公辅抬头,像是看到寂静的深夜里,一如既往的赤诚火焰。
“运动会时,咱都在山东见过冻掉脚趾的明军。”
他转身时烛光在眼窝投下深影。
“你可知为何叫他们更名红袍安定军?安定二字,先要安士卒之身,方能定天下之心。”
黄公辅哑然,心底也终于确定了一个事实。
里长如今仍如初见。
他甚至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会为了理想和信仰坚持到如今的程度。
他又看到这位红袍军之主身上破了洞的棉衣,里面缝缝补补,已混杂了不少芦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