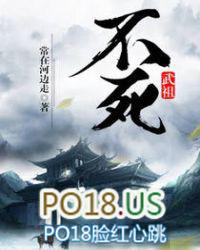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世子求你别这样免费阅读全文90章 > 第49章(第3页)
第49章(第3页)
说话间,他顶着所剩无几的意识起身,结果因为身子太乏,在谢时深身上扑腾半晌也没站起来。
谢时深紧咬着牙关,被他蹭得浑身不适,只好把人抱在怀中锁着,将那颗沉重的脑袋按在肩头。
鹿厌疲惫靠着,一动不动像条咸鱼,双手垂落在谢时深的身侧,温热的呼吸洒在他的颈窝,似在呢喃着什么。
谢时深拧了下他的湿发,听见嘀咕声后转头看去,嘴唇不慎触碰到他的额头,拧发的动作顿住,视线全然落在这张渐渐沉睡的脸颊上。
良久,静谧的浴室只闻一声轻叹,一抹身影从水中站起,抱着怀中人离开了水汽氤氲的浴池。
次日一早,鹿厌从刺眼的阳光中转醒,他眯着双眼掀开被窝,窗口吹进一阵秋风,寒意令他打了个冷噤。
他揉了下眼角,终于摸索爬出被窝,双脚刚沾地,他却发懵坐在榻边,久久没能反应过来。
为何他又在世子的榻上了?
他扭头回看床榻,空无一人,被窝只有自己的余温,他细细回想昨夜发生的一切,记忆似乎中断在浴池里,隐约只记得自己要去歇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思来想去也没个所以然,鹿厌也懒得费劲,心想也不是第一次留宿,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泡澡后的身子异常酸软,鹿厌从榻上起身,用力伸了个懒腰,拖着脚步去洗漱。
怎料片刻后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他连忙将衣袍穿好,赶在敲门声响起时打开房门,当看见来人脸上的着急时,他连忙问道:“刘管家,发生何事了?”
刘管家道:“小鹿,昨夜京郊可出事了?为何有人今早去官衙状告谢家?”
“什么?”鹿厌皱眉,“世子可下朝回来了?”
两人离开了明华居,刘管家脚步匆匆道:“世子在回来途中,但此事已经传遍京都,恐怕很快便会传到宫中。”
鹿厌脚步顿足,“传开了?”
刘管家道:“不错,此事乃下人回府告知的。”
鹿厌挠了挠头,努力冷静下来,细细回想昨夜之事,总觉得事有蹊跷,直到他记起府中另一人,忽地取出玄尾扇,转而叮嘱刘管家道:“你派人去打听官衙的情况,等世子回来及时禀报给他。”
说罢,他转身朝着客房的方向跑去。
当他站在连衣的厢房门前,用扇子轻敲少顷仍不见回应,遂后撤一步,果断抬脚踹去。
“嘭”的一声,鹿厌踹开后快速入了内室,掀开伪装的被褥瞬间,果不其然人去楼空。
能把如此私事一夜传遍京都,除了内鬼别无他人。
他折身搜寻屋内,直到脚下似踩到异物,低头一看脸色瞬变。
只见他弯腰将地上一截断裂的扇骨捡起,顺着桌底看去,全是被蓄意破坏的周边残骸。
他将碎玉握紧在手,清楚为时已晚。
昨夜中秋,连衣借落水不适之由留在府中,时至佳节,谢家并未对此人严防死守,结果被他趁虚而入摆了一道。
鹿厌拿起碎玉起身,余光见一抹身影出现,侧头看去,入眼见身着朝服的谢时深出现。
“世子!”鹿厌拔高声喊道,疾步走出厢房,“大事不妙,人跑了。”
两人迎面上前,谢时深来时已得知事变,却一如往日沉静,仿佛皆在掌握中,唯有眼下的些许乌青显得格格不入。
“无碍,小事一桩。”他抬手拨开鹿厌嘴角的褐发,“昨夜睡得可好?”
鹿厌愣住,未料他竟关心起这等小事在先,迟疑了下才说:“睡得很好,叨扰世子了。”
谢时深道:“那就好。”
鹿厌礼尚往来问:“那世子睡得可好?”
谢时深沉吟,昧着良心道:“我也睡得好。”
可话音刚落,他又道:“话说回来,若你不嫌明华居冷清,日后可否常来?”
鹿厌细看发现他神色疲倦,有些担心问道:“世子怎么了?”
谢时深揉了揉鼻梁,倦怠说:“说来惭愧,近日府中不太平,我睡得有些不安,要是有人陪着我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