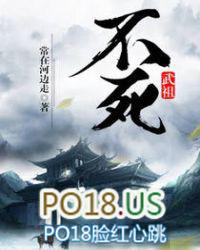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哥哥人鬼殊途你知道吗by山行禾尽txt > 第七章 生死的缘分(第2页)
第七章 生死的缘分(第2页)
他挑一挑我的下巴逗弄宠物一样挠,开心了,又顺从地改了措辞:“你和我有生死的缘分,懂吗?你活着,身体里流着的血能留住我。”
我懂了。
兄弟之间总有无形的羁绊,尤其是同时在娘胎里孕育的同卵双生子,更是缠绕着细密的、看不清的线把我们的灵魂拘在一起。
所以才会有传闻中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那是一种灵魂同频。
我哥死了,只是他不愿意走。所以那些看不清的丝线和看得清的血管成了束缚住他的东西,把他捆在我身边。
至于他为什么不愿意走,我姑且信他的说法——他觉得留在我身边有趣。
我转身往三楼走,掏出钥匙打开我家的门。
我妈不在家,房子里没开灯。
推门换鞋进卧室,门锁刚落下我哥迫不及待地和我接吻,把我推到床上整个身子压下来重量实打实他在我身上,压得我肋骨和肉撞在一起死疼。
房间里拉着窗帘,昏暗的光线照不进来更是一片漆黑。我哥这时候不像鬼,像是一片影子,盖在我身上想把我同化吞噬。
他按住我的手腕膝盖分开跪在我身体两侧,俯身纠缠着我的唇瓣把教室里没尽兴的性欲重新发泄出来,从一个鼻尖擦错的吻开始。
“你像有性瘾,如果不是鬼,我会带你去检查。”
我趁他微微拉开一段距离睁开眼睛看我的时候吐槽他性欲真的太强,他却只是重新吻上来,不回我的话语,把我的唇瓣当成什么小孩子的吸吮玩具或者小狗的磨牙棒一样又舔又吮还咬两口。
等他尽兴了,扯开唇,我嘴巴是什么红肿样子不用摸都知道。
只有他开心了,舒服了,尽兴了,才会有心情慢吞吞调戏我作为人比他慢一拍的脑筋:“你自己说我是色鬼转世,性瘾不是色鬼必不可少的吗?”
说到这个,他就来兴趣。凑到我下巴上亲一口,摊开我的手指和我十指相扣深深压进柔软的床里,嗓音低沉好听:“我还应该做什么?内射?持久?一天三次一周七天?你给我讲讲一个色鬼的守则。”
呃。我还得给他讲怎么操我吗?
我该给他讲每次他龟头进入到肠道的哪个位置我会很想喘吗?
我该说他内射时我面红耳赤想要跳脚吗?
还是我该说一周七天一天三次我明天就精尽而亡和他做亡命鸳鸯,墓碑比邻而居一人坟头插几朵孤零零的菊花?
这些话我说出来他估计会摸摸我的额头问我是不是被他操得过猛,生病发烧了。
他的骚话我不该理,只是每次忍不住去细想,都会膛目结舌刷新他在我心里的下限。
“你的坟在哪里。”我立刻转移话题不和他讨论这些有的没的情情色色的东西。
“想去啊?”我哥摸我的脸,额头的红痕抵在我额头上来,那道深红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的额头也只是温度稍微比我低一些。呼吸交缠,他说的话热热的轻轻地落在我的嘴角,我只能嗯一声表示我确实是有点兴趣。
比起想看他的坟,我更想知道他叫什么。
没人告诉我我哥的名字,妈把它废弃,灰尘把墓碑上的名字填积。世界上好像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来过。
我也会心有戚戚,思考他到底是不是我的幻想,或者分裂出的第二人格。
所以我喜欢他触碰我,吻我,和我舌尖交缠,和我十指相扣。我不敢说喜欢和他做爱,但我能够说和他做爱的时候我会觉得真实,明白他的确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陪伴在我身边,即使用性交的方式。
我哥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觉得我是有点想知道他的名字。
“行吧,我带你去看。”我哥抓着我的手在我掌心顶蹭了好几下性暗示非常明显,还是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