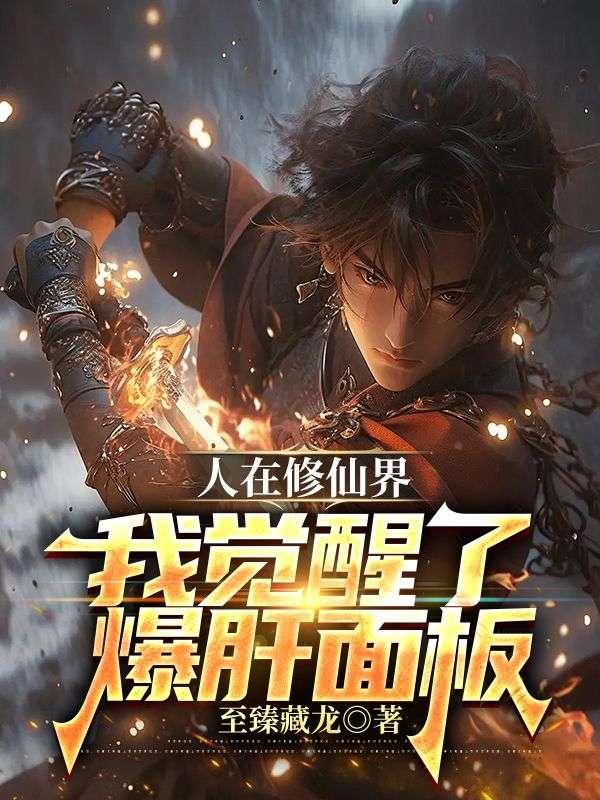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白团是什么意思 > 老爹是谁(第3页)
老爹是谁(第3页)
阿浅愣了愣,缓缓抬头。
“你别担心,他……就是个个子比较高,声音比较大,爱喝酒,但其实很温柔的人。”以藏一边比划着,一边努力挑选着不吓人的词汇,“你想,他连我都敢收,你就知道他有多宽容了。”
以藏试图通过贬低自己增强阿浅的自信心(bushi)。
阿浅歪着头,像是在认真理解以藏说的每一个字。
她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反应,但内心却在悄然翻涌。
讲心里话,她现在心里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害怕。
甚至她有些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要露出那种微妙的紧张神情——像是要带她去见某个特别难以接近的大人物一样,谨慎、局促,连一向从容不迫的马尔科哥哥都有些语气不稳。
是担心她不被船长接纳,被赶走吗?
这个可能性,她当然想过。但说实话——她并不觉得自己非得被接纳。
她本来就不是属于这里的人,不是吗?
她只是一个意外掉进来的异乡人,一只走错了巢的小鸟,一段被捡到的未知碎片。比起什么归属,她已经习惯了做一个“过客”。
被抛弃、被放弃、被忽略——对她来说,这些都不新鲜。
在她过去的记忆里,离别和失去是常态。她不是那种会指望奇迹发生的小孩,因为她知道,奇迹通常不会降临在她这样的人身上。
她甚至已经练就了一种奇妙的钝感:当有人对她好时,她会感激;但一旦那些温暖消失,她也不会觉得特别痛苦。因为她早已为离开预留好了余地。
可即便如此,阿浅还是有点期待。
也许是因为,以藏哥哥试图用各种可爱的方式来缓和气氛——比划、开玩笑、甚至故意贬低自己说“就我这种人都能被收留,老爹当然好说话啦!”那种用力轻松的语气,其实暴露出他对这场见面的重视。
也许是因为,她从这些哥哥们的言语和行为中,读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是的,他们从未逼问她的过去,从未强行突破她的沉默,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她慢慢有了“今天”“明天”这样的念头。
她有点想知道,“未来”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她好奇。
那个被称为“老爹”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是会发出“咚咚咚”笑声的巨人吗?是像萨奇哥哥说的那样,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声念叨“家人就是一切”的大块头吗?
他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却又愿意弯下腰,给一个孤儿一个家吗?
她突然想起,萨奇哥哥曾在厨房一边炖汤一边和别人说过——“老爹收留了我们,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还有孩子像他年轻时一样,在世界上孤零零地活着。”
只是当时她情绪不佳加上语言还不是很熟悉,没能反应过来。
而她也隐约听到过,以藏哥哥其实也曾是一个流浪的孩子。
原来啊,船上的人们,大多数也都和她一样啊。
所以他们才那么紧张吧。担心“她”被赶走,也担心他们共同守护的小家,没办法容纳她。
他们在意她,也在意这个家。
想到这里,阿浅垂下了眼睫,指尖无意识地搓着袖口,轻轻地、慢慢地,像是在酝酿一种她从未真正说出口的愿望。
她想看看他。
不是为了被接纳,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只是,她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让那么多“没有家的人”,愿意称他为“老爹”。
她从未拥有父亲。
但她想知道,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