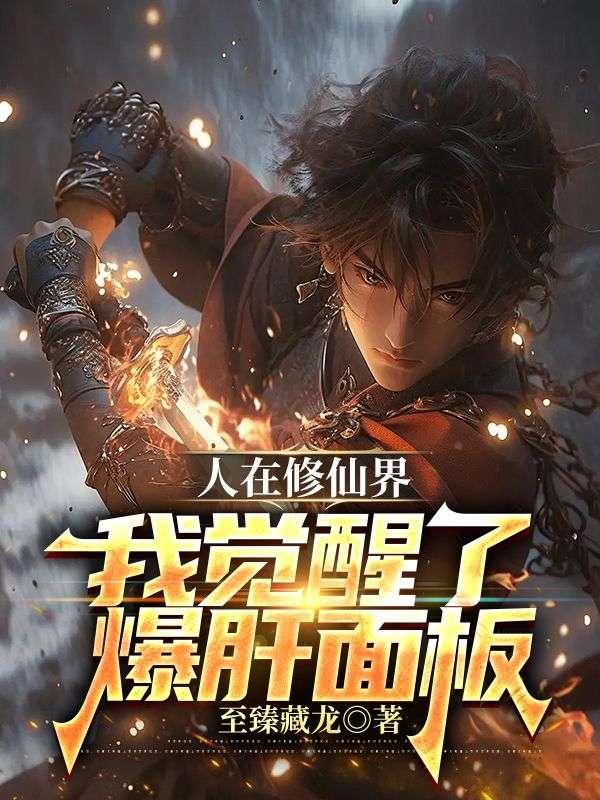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白团的实力 > 以藏悄悄关注以藏悄悄心疼(第3页)
以藏悄悄关注以藏悄悄心疼(第3页)
阿浅后来才慢慢知道他的名字。他很安静,不会用很大的声音叫阿浅,身上总是有一点点香香的味道。像是花的味道,又像是颜料。
他总会带回来不同颜色的花,趁她睡着的时候,悄悄地放在她的小柜子上。有时是一朵金黄色的矢车菊,有时是一束碎碎的粉白满天星,也有一次,是一瓶浅紫色的风信子。那颜色美得像夜里不敢吱声的梦。
其实最开始,她也并没有睡着。
第一次送花的时候,阿浅正在发呆。眼睛空空地望着天花板,脑子像被水泡过的棉花,一团湿冷的、沉重的。那时候她还不习惯白鲸号上安静的夜,更不习惯有人类靠近的脚步声。
她听见门吱呀一声轻响,像风拂过木门的声音。然后,有什么柔柔的、彩色的东西从她眼角的余光里飘过去了。她没有动,也没有眨眼,只是静静感受那道影子离她越来越近——然后,又轻轻远去了。
当他离开后,房间里只剩下一阵淡淡的清香。
第二次送花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与他有了短暂的视线交错。
她是从指缝中偷看的。
那天,他穿了一件紫底金纹的和风外衣,头发高高束起,用红色发绳轻轻扎着,耳垂上挂着两个银色圆环,闪着一点点光。他眉眼极长,眼角微挑,本该显得冷傲,却偏偏透着种慵懒而温和的神情。他走路很轻,像是踩在云朵上。
身上的颜色鲜艳得几乎不合时宜,但他本人却一点都不张扬。那些色彩像是主动围着他打转的花,缠着他不肯离开。
阿浅想,他是一个会被颜色喜欢的人。
他把花放下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了一会儿。她能感觉到,他在看她。
也许是在确认她有没有醒。
也许是在担心她今天有没有哭。
阿浅没有动,像以前在很可怕的地方学会的一样,把自己变成“沉默”的东西。她知道,他或许怕吓到她,所以她一直假装睡着了。
但心里那种很微小、很微小的东西,开始慢慢动了一下。
像是一直缩着的猫耳朵,悄悄抖了抖。
之后阿浅没有再哭。不是不难过了,而是觉得累。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像隔着玻璃一样陌生又遥远。医生哥哥——阿浅听见别人叫他“马尔科”——偶尔会试图跟阿浅说话,但阿浅只是摇头。不是不想回应,而是做不到。
阿浅说不了话。阿浅从来都说不了话。
但现在,阿浅更说不出阿浅心里的害怕。
他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点。某天的早上,有人悄悄放下一本厚厚的小册子在阿浅床边。封面画着好多奇奇怪怪的符号,还有一行阿浅看不懂的文字。旁边压着一块松软的椰子糖,还有一张小纸片。纸片上用图画画了一个人拿着这本书在看书,然后笑着对着另一个人打招呼。
阿浅偷偷翻那本小册子的时候,有点怕别人发现阿浅不懂。阿浅怕他们会觉得阿浅“笨”,像以前的那些人一样。
不过,这里的人好像……不会那样看阿浅。
他们不会嘲笑阿浅看不懂字。甚至还会在纸条上画图解释一个词的意思:比如“船”是画了一艘摇摇晃晃的小船,“太阳”是一颗大大的黄圆圈上面画着笑脸。
阿浅学得很慢。有时候一页书要看两天。但阿浅记得那些图,一点点试着对应它们下面的符号。
阿浅看着那些扭扭曲曲的符号,再看看窗外懒洋洋晃动的海面。
风还在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