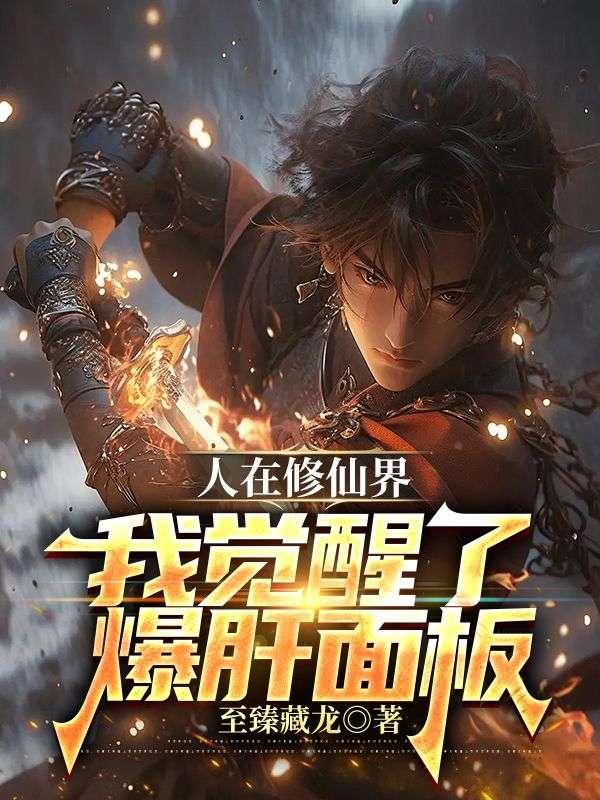三五文学>拂了一身满桃籽古言结局 > 第77章(第2页)
第77章(第2页)
他的手便在那一刻松开了,好像是被她的眼泪烫出了可怖的疮口,又好像仅仅觉得她无药可救;她为他的离开庆幸,心底最隐蔽的角落又泛起一阵卑劣的绝望,下一刻暴虐的气息骤然降临、是他一把将她狠狠拽进怀里,千般幻景刹那颠倒,一切禁忌便在那一刻土崩瓦解零落成泥。
……他在吻她。
像殊死的困兽一样撕咬,像离水的孤鱼一样挣扎,没有哪怕一丝情浓时的温存缠绵,只剩末日来临前孤注一掷的宣泄——她感到更剧烈的痛,一颗心在胸膛里疯狂地跳动,汹汹激荡的醉意令她难分虚实真伪,他却偏偏逼她睁开眼睛看清他那时陌生的模样。
他紧紧扣着她的腰、甚至毫不怜惜地扼住她的脖颈,艰难的喘息令她正似涸辙之鲋,每一丝生机都需仰赖他的垂怜才能窃取;他好像当真想掐死她,一双向来平静的冷眼却在那时红得像血,某一刻她忽然懂了,那时他想拉她一起下地狱。
暴烈的爱意在无路处降临,猛然放开的桎梏却令她重获新生,他给她以苦痛的烙印,一个落在颈间的吻便令她深深战栗。
“三哥——”
“……三哥——”
她不停唤他,其实也不知是在挽留还是拒斥,他的失控便在那一刻到达顶点,“碰”的一声巨响炸开在她耳边,随即整个天地都陷入一片僵冷的静默;他将头埋在她的颈窝,水榭的木柱已然深深凹陷,她的余光看到他青筋迸发的手背和血肉模糊的指节,剜心般的疼痛令她几乎遗漏了落在自己胸口的一点湿润的热意。
“疏妍……”
他的声音像戴着枷锁,即便每走一步都要削去一块他的血肉也还是拼命向她靠近,她所熟悉的柔情也在那一刻重现,小心翼翼的亲吻落在她的唇角,抚摸她脸颊的手颤抖到难以自抑。
“就这样吧……”
他轻轻为她拢起凌乱残破的衣襟,终究一错再错将她紧紧拥在怀里,堂皇的重复像是梦中的呓语,状似与她相同可实际却又迥然相异。
“我们之间……就这样吧。”
光祐元年四月廿三,金陵雷霆忽至,暴雨数日不止。
昨夜阴平王府笙歌不歇通宵达旦,前去赴宴的文武官员个个喝得昏天黑地人事不省,施、杜二人最是尽兴,与阴平王推心置腹把酒言欢,最后双双醉得爬不起来、索性便在王府客舍留宿过夜。
天将明时大雨倾盆,声声惊雷隐于黑云之后,施鸿头疼欲裂被吵得不得安眠、以衾覆耳又觉声响愈大,心道怪哉起身一看,只见窗扉之外鬼影重重,那阵阵扰人的闷响哪里是什么天边惊雷、分明……分明是寸寸逼近的刀剑甲胄!
他一个激灵翻身而起,下一刻房门却被重重一脚踹开,几个一身重甲的士兵持刀而入、看形制正是出自南衙卫府的禁军;宿醉的头脑混沌一片,来不及思考当前形势便直觉与人打斗起来,可惜双拳难敌四手、不多时便被狠狠击倒反扭了双臂。
“我乃岭南节度使——朝廷三品大员——”
“尔等受何人指派——还不速速将本将放开——”
嘶吼叫嚣十分卖力,可惜被慑人的雷声一遮也是喑哑不清;踉跄着被一路推进屋檐之外的暴雨,好友杜泽勋已同样被反捆双手跪在庭下,站在他面前的两个男子十分面善,赫然正是几日前方才见过的娄氏兄弟。
“……娄风!娄蔚!”
施鸿勃然大怒,满面雨水的模样实在狼狈不堪。
“你们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如此辱没上官!”
“我定要去御前参奏——要你娄氏满门谢罪——”
他似极爱提及娄氏一族、言语间的鄙薄轻慢更令人无法忽视,娄蔚闻言眉头微锁,兄长娄风却是面无表情;他同样立在雨里,背后是一望无际的黑沉天幕,注视施鸿的目光冰冷得像在看一个死人。
“御前参奏?”
他冷冷一笑,神情戏谑又暗藏快意。
“那就要看上官能将这条命留到几时了。”
话音刚落一道飞火穿云而过,雷声隆隆接踵而至,施鸿心猛地一跳,不敢置信道:“你……你敢杀我?”
娄风似笑非笑不置可否,居高临下的模样却更令二使不安羞恼,便连一向内敛持重的杜泽勋都忍不住开始高呼嘶喊,嚷道:“我要见太后!我要见陛下!——我等身有战功并无罪责,朝廷岂可残害忠良草菅人命!”
施鸿一听立刻附和,娄风充耳不闻、只漠漠挥手令麾下将士将两人扭送出王府;撕扯吵闹间阴平王终于是到了,宿醉之后衣衫不整、一张老脸更是黑如锅底,此刻见娄氏兄弟竟在自己府内拔刀亮剑,当即气得唇色发紫,怒喝:“反了!反了!”
“本王乃卫氏宗亲!便是天子亲临也当称我一声皇叔!你们竟敢带兵闯我王府,是当真要造反叛乱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