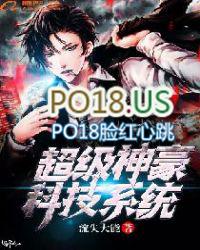三五文学>满庭芳周邦彦 > 21第21章(第1页)
21第21章(第1页)
送走馥娘后,林稹心不在焉的坐在榻上发呆,呆坐了一会儿后,她匆匆起身,直奔祖母的松鹤院。
一入内,就瞧见祖母正素衣葛布,端着木盆,取了水瓢,伺候她的几分地。
“祖母。”林稹帮着接过水盆,浇了一小分金皮瓜地。
只是她那水舀得一瓢多,一瓢少。余氏见了就心疼她的金皮瓜,叹气道:“心不在焉的,可是出了什么事?”
林稹稍显迟疑。
一旁伺候余氏的邓妈妈会意,当即起身:“老夫人,这会儿都快吃午饭了,我带人去厨房取些饭菜来。”
“清淡些就好。”余氏点头,又拄着膝盖起身,对林说,“随我一道进来罢。”
林稹赶忙去扶她。
两人进了屋,遣散了女使,低声道:“今日馥娘来寻我,忽而提到我的未婚夫婿,敢问祖母,可有此事?”
余氏诧异地看她一眼,又蹙眉道:“你这孩子,提起这些事怎么也不害臊?”"
林稹不以为意:“祖母这就说笑了。乡下人家,打赤膊的都瞧过了,提一提婚事有什么好害臊的?”
“再说了,日子是要我自己过的,我今日若害臊不敢提,万一所托非人,日子过得不好,难道要怨我今日胆小吗?”
见余氏神色稍显和缓,林又放软了声音,哀哀道:“祖母,我骤然得知此事,一时无措,又有些。。。。。。”她像是有些难以启齿,于是重复了第二遍,“祖母,我有些害怕。”
余氏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只管用自己干枯的手掌抚了抚她的鬓角,轻声哄她:“女人都要有这一遭的。”
“可我不想离开家。”林稹神色稍显低落,摇头道,“我不想去个陌生的地方。”
余氏叹息一声,只好连连哄她:“放宽心,那是你祖父定下的,你祖父看人的眼光极好,必不会亏待了你。”
林稹问:“是哪家?在京里还是湖州?”
“恰好在汴京。”余氏缓缓坐下,“应当是隔壁的韩相公家。”
林稹一惊:“相公家?”话音刚落,她眉头皱得死紧,又苦笑道:“人家是宰相、我家却……………门不当、户不对的,我嫁过去,日子只怕不好过。”
余氏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这会儿面上也有些忧色,只能勉力安慰道:“不至于,当年我们俩家是通家之好,韩相公那人我也见过,是个说一不二的,必不至于亏待了你。”
林稹点头称是:“的确不会亏待我。。。。。只是也不一定会娶我做孙媳妇。”
余氏心里也有这个隐忧,只轻飘飘驳斥了一句:“得胡言。”
林稹也不怕,只管分析道:“我虽不知这位韩相公与祖父有何渊源,但我知道祖父丧礼的那几日,韩相公家并未遣人来祭奠。”
余氏叹息道:“不怪他。彼时他应当在外地任官,双方一去几千里,报信都来不及呢。”
“话虽如此,只是当年在湖州,逢年过节的时候也并未接到韩家节礼啊。”林稹试探道,“既然两家十余年不曾往来,这桩婚事约莫是不成了。”
余氏笑着摇头:“你不知道罢了,韩家的节礼都是送来沂哥儿这儿的,再由沂哥儿挑拣过后送去湖州。”
林稹心里发沉,硬撑着辩解:“既是两家有往来,那怎么十几年都不曾提过婚事?”
“我原想着等淮哥儿专心把这科考完。中了自然好,纵使不中,也能捐个员外郎做做。如此一来,你爹有了官身,才好跟韩府提你的婚事。”余氏打趣道,“谁知道你今儿就惶急慌忙找来了。”
一切都要为了考生让路。
这很正常。
林稹勉强挤出个笑来,“可韩家高门显贵,要是他们不认这桩婚事怎么办?”
“不必臆断。”余氏摇摇头:“韩相公就在隔壁宅子,届时我寿宴,请他家女眷赴宴之时稍加探问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