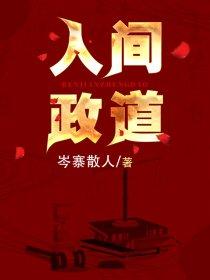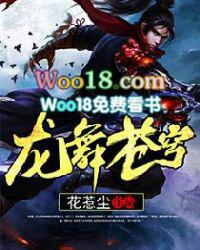三五文学>载我以生 > 子夜四时歌三(第2页)
子夜四时歌三(第2页)
楚王这一手,既堵了天下悠悠之口,又借机拔除了她们安插最深的钉子,狠辣精准。她身后侍立的亲信低声道:"萍姨,钱、孙二人。。。。。。"
“弃子罢了。”崔萍声音平淡,听不出喜怒,“楚王既要她们的人头堵窟窿,我们便给她。传话进去,让崔邺安心。事已至此,她该知道怎么做,才能保亲族最后的体面。”
她将凉透的茶盏随手搁在窗台,目光投向远处那辆悄然离去的青篷小车,眼底掠过一丝阴鸷。
裴家女郎,好一个坐山观虎斗。
车轮驶过石板路,辘辘声在寂静的巷道里回荡。裴照野重新阖上眼,指尖在袖中那枚冰凉的墨玉棋子上摩挲。
崔氏的反应,想必已在酝酿。这七颗人头,不过是棋盘上被扫落的几粒尘埃。
-
宗庙别院,第三日。
寒风刮过高墙,呜咽如泣。院中古柏的枝桠在墨蓝天幕上投下张牙舞爪的剪影。
萧允贞独坐冰冷的书案前,案上堆着抄录好的厚厚一叠宣纸,墨迹已干。
他脸色苍白,眼下已有淡淡青影,他的确许久没有如此乖顺安分过了。
书页上字里行间的规训伴随了他整个幼年时期,辞令仪态,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爹爹将这些贤德规范奉行得极好,他自然耳濡目染,修之习之,绝不有辱皇室体面。
但愈是贞静,愈是温良,便愈要受人欺凌。
凭什么?
崔氏权倾朝野,一手遮天,父君便可以有蛇蝎心肠,便可以祸乱宫闱,致爹爹于死地?
有哪一处贤良淑德?
萧允贞今二十有二,仍不解其中之意。
爹爹亡故后,他再不愿循这些规矩。世人说他离经叛道,毫无德行可言。不过是夜登酒楼,醉后唱了些女欢男爱的俚俗艳曲,就有忠臣在前朝参他一本,他只觉好笑,拟了些荒诞诗文供人在花楼赏玩,大骂崔氏门生是□□草包之流。
他开始蔑视礼法,成日饮酒作乐,一掷千金,不参集会,甚至连母亲的传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
他知道母亲疼他爱他,出于对爹爹的愧疚,几次三番容忍他。然舆论倾轧,排山倒海,他还是被母亲的一道圣旨,指去下嫁已凋零失势的长孙氏女郎雅荣。
那女郎并无半点过错,长孙氏更是因成山的丰厚嫁妆改善了经济状况,对他恭敬至极,可谓感恩戴德。
他儿时自然憧憬过姻亲,期盼能嫁予才学修养皆为上乘的正人淑女,最好再如母亲一般英武、如姐姐一般雅量,若能得这样妻主,便是他人生之幸事。
但萧允贞实在气不过。他也有那么一瞬间想过和长孙雅荣共度一生,相妻教女。看着她那副脑袋空空的谄媚模样,他一肚子闷火根本无处可施。长孙雅荣实在木讷,又胸无大志,若是就这样浑浑噩噩一辈子,他萧允贞才真是早该随爹爹一并去了。
他知道自己生为男儿,无力向崔氏挥刀,朝堂之事腌臜至极,能避则避,他才不愿去做第二个李隆基。但姐姐可以,姐姐聪慧,能容人事,通道义,这太女之位大姐坐得,姐姐又如何坐不得?
他是皇子,父家柳氏于前朝遭受牵连,元气大伤,唯一的筹码只余下妻家。长孙氏毫无益处,甚至可能拖累姐姐前程。
萧允贞思虑良久,还是精心设计杀了长孙雅荣,包装成那女郎自己惹上的意外,再给一笔天价赔礼,封住长孙氏的嘴。他连孝期都没守过几天,便被母亲召回京城,从此成了浪荡恶毒的鳏夫。
大婚那天他来了癸水,她二人甚至连妻夫情分都未能坐实。他眼看着长孙雅荣在他跟前咽过气去,死状平静,那张蠢脸和生前并无二致。
他记得自己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她还留有余温的脸颊,这感觉如此陌生,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感。全然不似爹爹那般,饮了鸩酒,呕出的鲜血溅到锦袍之上,阖上双眼前还要平添几分烧心的苦痛,身体却冰冷僵硬得如同腊月的石头。
这是他第二次亲眼见证她人故去,也是他第一次杀人。
他想,他由着性子赐她人一死,与父君也并无差别。
从前世人参他狂悖,疯癫,离经叛道,他置若罔闻。那天,他觉得自己彻彻底底成了痴人,不过倒也没什么不好。
他陷入思考,回想起长孙雅荣待他恭恭敬敬的霉样,无聊透顶,不如裴含章半分趣味。那日在终南山巅,她盛装端坐,在万千目光中沉静如水的模样,远比守在那死寂的郡君府中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