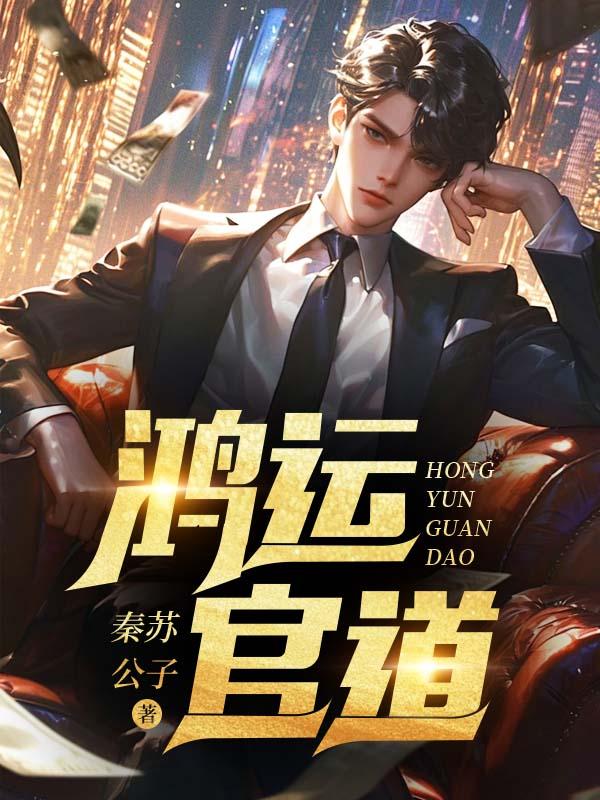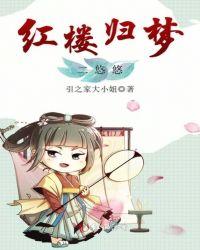三五文学>大唐我真想当昏君啊 > 第153章 突破口(第1页)
第153章 突破口(第1页)
李持本是举人出身。
唐朝初立时,李渊为稳固社稷,既留用隋室旧臣,又广纳寒门才俊。
眼瞅着已经贞观十年,门第的成就越来越严重,官场晋升之路宛如天堑。
举人出身者与进士及第者相较,仕途境遇云泥之别。
李持能从蒲州司仓参军调任蓝田县丞,全因任内考核优异。
那年蒲州大旱,他硬是跑遍了三十六乡,开仓赈济、均平粮赋,
呈报的灾情奏疏上还沾着已经干透的黄土与汗渍,恰被李世民留意,这才有了升迁之机。
然而,三十一岁的李持并不满足于此。
他的房间里,常摆着《汉书》,“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八字被他圈了又圈。
但是无进士出身的他若想再进一步,除非立下不世之功,要不然就是寻得坚实靠山。
李世民的大腿虽粗,他却不敢轻易攀附——毕竟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不是九族消消乐,就是岭南游。
然而,事情很快迎来转机。
某日下午,一名来自魏王府的属官,来到县衙,递出盖着玄色私印的密信,上面的蜡封都尚有余温。
所求之事简洁明了:探查蓝田县隐秘,事成必有重赏。
李持心如明镜,朝堂之上太子与魏王的储位之争,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潮汹涌。
前任县令苏策深得太宗宠信,更是太子李承乾的心腹。
明眼人都看得出,陛下将苏策派往长安,实则是试炼诸位皇子应对政务的能力。
李持当夜便翻出历年邸报,逐字研读与魏王有关的奏章。
押注魏王若能成功,他日飞黄腾达不在话下;
可他亦深知,一旦押错,便是万劫不复——毕竟历史上多少人因为站错队,导致家族因此覆灭。
现实却给了李持沉重一击。
蓝田县早被苏策经营得如铁桶一般,青砖灰瓦间盘根错节的势力网,将李持困在权力真空的漩涡中央。
他名义上接手政务已过月余,每日批阅的却尽是些无关痛痒的文书,那些真正关乎县治命脉的机密卷宗,始终锁在福伯檀木匣里,连封皮都不曾见着。
晨光未熹时,县衙后堂便传来算盘珠的脆响。
地方营造的匠作账簿、赋税征缴的银钱流水、城防部署的兵械明细,全在福伯枯瘦如柴的手指间流转。
福伯这老油条算盘打得贼精,跟着苏策那些年,早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学了个十成,连眼里算计的精光都和苏策如出一辙。
李持三番五次要求交接,得到的却是福伯皮笑肉不笑的敷衍:"新县令尚未到任,一应事务还需老身暂为周旋。"
他在案卷堆里发现过盖着苏策私印的密函,也见过福伯偷偷将成箱的粮册装上马车。
最令他脊背发凉的是那个雨夜,他冒雨查巡牢房,竟撞见福伯与两名金吾卫在偏门密谈。
福伯腰间那枚五品官员才能佩戴的玉佩,在灯笼光影下泛着冷光,玉佩上的螭龙纹与金吾卫腰牌上的纹饰隐隐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