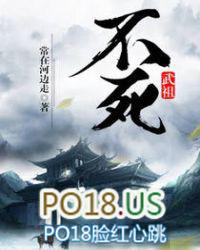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东宫笼中雀雾颚白免费全文阅读 > 第93章 番外 少年时1(第1页)
第93章 番外 少年时1(第1页)
永庆十二年,北帝遇南方刺客行刺,险些丧命,帝大怒,命南方诸国送王太子前来为质,否则兴兵南下。
南方十二国无力抗衡,只能派使团送来王太子。
各国质子均安置在国子监旁的鸿胪寺中,并将与一众北朝皇子皇女同读于国子监。
而在各国质子来国子监就读的第一天清晨,大门前便乌泱泱站了许多人,为首的两位皆一身华服,比之后面的人明显身份尊贵,其中一个稍微瘦高的少年有些顾虑道:
“五哥,你说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惹得太傅们不高兴?”
而另外一个稍壮的少年则不知为何极度有信心道:“老六,这你别管,尽管做就是!”
“那就好。”
有了兄长打包票,瘦高的那位松了口气,转眼看了眼一旁的新修的狗洞,“那待会儿可就有好戏看了!”
话音一落,身后便有人喊:“五殿下,六殿下,他们来了!”
五皇子和六皇子闻声立马朝街道远方看去,却见几驾马车朝他们的方向驶过来,停在国子监门口后,每辆马车中都跳出好些少年,男女皆有。
他们虽与国子监门口的人年龄相仿,可衣着打扮,与五官模样,与下马车的少年们有明显的差异。
五皇子身后的随从不客气喊:“见到两位殿下,你们怎么还不行礼?”
按理说,对方虽为北朝皇子,可他们作为一国太子,怎么就一定是他们朝对方行礼了呢?
除非对方乃是北朝太子。
他们并没有见过北朝太子,于是下意识认为眼前两人中的一位乃是太子,一众质子纷纷行礼:“我等见过太子殿下与皇子殿下。”
可此言一出,在场一片哄笑。
见质子们不解,六皇子道:“你们行礼行大了,我与我五哥只是皇子,你们对我们这么行礼,那待会儿如何向我们太子殿下行礼?”
质子们反应过来被耍了,可现在他们皆为人质,人为刀俎,他们为鱼肉,无力回击,只能咽下羞辱,内心宽慰自己只要忍过这次便好。
但第二次羞辱很快就降临。
“你们以后都不准从正门进。”
六皇子大言不惭地道。
质子们不解:“我们不从这里进,那要从哪里进?”
六皇子指着大门旁:“喏,这就是你们以后进出的地方。”
看着那需要人弯腰,才能勉强进的小门,质子怒道:“这分明就是一个狗洞!”
五皇子嚣张打断道:“就是要让你们钻狗洞又如何!你们难不成想造反?!还是说,当初我们父皇遇刺,便真是你们这些南蛮的手笔!”
他一下子把话题扯到北帝遇刺上,先前还愤慨不已的质子们纷纷清醒过来。
他们这批质子谁在这北都闹起来,那么北朝率先对付的,可能就是他的国家。
而就在他们咬牙要蜷起身体,从“狗洞”小门走过时,一道声音却拦住他们:
“这便是堂堂北朝的待客之道吗?”
所有人循声看去,却见南业国王太子身边站出一个儒雅的少年,他身后的王太子吓一跳,低低怯急地喊了一声“君同”。
六皇子皱眉:“你是谁?”
少年走上前去,不卑不亢道:“在下冼君同,是随我国王太子一同前来北朝做客的。”
五皇子从上至下看着眼前的儒雅少年:“你刚刚说什么我北朝的待客之道?你难道是在不满吗?”
名唤冼君同的少年问:“君同不敢,只是君同从来只听闻,只有狗请客,方才请客人从狗洞进。”
此言一出,顷刻把在场所有人噎得一句话说不出,北朝皇族与南国质子两边的形势顿时逆转。
“你——!”
五皇子脸色顿时怒耻交加,刚想冲上去给对方一顿,对方却掠过他,来到尾上的一辆马车前,行礼道:“太子殿下,戏看够了,是要出来主持大局了吧?”
车中沉默了片刻,一句话传出来,宛如鞘中王剑绽出一线锐利刀芒:“姓冼?冼松臣是你的谁?”
冼君同立即道:“是臣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