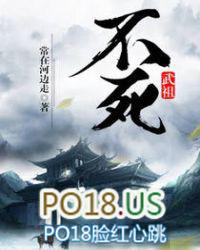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复生攻略快穿by快穿免费阅读 > 3040(第2页)
3040(第2页)
说完,没有一丝一毫地停留,邵逾白直接转身离去。
陈和见状,立马高喊退朝,众臣跪拜,只留老臣跪在原地,哀叹不已。
……
回大明殿的路上,不需要任何提醒,余逢春自觉地从另一边上轿,坐在邵逾白旁边。
感觉到旁边的晃动,邵逾白抬眸瞥了他一眼,目光藏在十二束旒后面,不动声色。
余逢春低头整理衣服,不理会他的目光。
等到太监抬起轿辇,朝大明殿的方向走去,余逢春才干咳一声,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把手伸过去,搭在邵逾白的手腕上。
“方才上朝时,江大夫不是已经把过脉了吗?”
邵逾白出声,将余逢春努力营造的无事假象打破。
余逢春没了办法,心中暗骂一声死孩子,继续糊弄:
“方才是方才,陛下上朝劳累,草民要再观察一下。”
话说的场面漂亮,可只要细看就知道,余逢春的手压根没搭在邵逾白的脉搏上。
邵逾白自然也清楚。
他低下头,盯着两人交叠在一起的手看了许久,片刻后哼笑一声,眸中含笑,先前从大安阁出来时的一身烦闷自然消解。
余逢春见状很满意,跟哄小孩儿似的拍拍他的手背,浑然不觉此举僭越。
跟在身后的陈和咂舌。
往日里,只要那位韩大人一提立后,陛下便会烦闷暴躁,一日不得展颜,旁人怎么劝都劝不好,连带着他们这些做下人的也乐不起来。
陈和本以为今日也会如此,没成想江大夫一哄就好,省了太多麻烦。
真是人不可貌相。
回到大明殿,邵逾白去换常服,陈和也跟着伺候,留余逢春在外面。
余逢春从心里计算着把多少次脉才能解毒,偶然瞧见和他一起被留在外殿的卫贤,想起早朝时注意到的异样,朝卫贤走去。
他笑眯眯地开口:“卫公公。”
相识几日,卫贤已经摸出了余逢春的脾气,知道他这么笑绝对没好事,心生警惕。
“做什么?”
余逢春道:“我观今日上朝时,陛下称丞相为师兄,这是为何?”
“你不知道?”
卫贤斜眼瞥他。
闻言,余逢春老实摇头:“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谁懂他一睁眼发现全世界都觉得万朝玉是他学生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别人就算了,邵逾白还真师兄师兄的叫上了,这是中毒,连带把脑子也给毒傻了?
余逢春心里的种种汹涌没有显到面上,卫贤以为他只是好奇,便勉为其难地回答:“陛下与丞相都曾随着余先生学习,是一门的师兄弟。”
“那陛下一直在朝堂上唤丞相为师兄吗?这是否有些……”
他没说全,但懂的都懂。
卫贤道:“丞相倒是劝过几回。但陛下坚持,就不了了之了。”
余逢春觉得自己真是一脑门官司。
理智上,他不觉得邵逾白会直接相信万朝玉的一番言辞,可情感上,余逢春实在怀疑自己的学生已经傻掉了。
“所以,”他费劲吧啦地组织语言,“陛下和丞相十分要好喽?”
卫贤闻言,笑了一下。
一张素来冷淡的脸上骤然露出微笑,本该是十分动人心弦的,可卫贤这抹笑,总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古怪,仿佛在讽刺,仿佛又只是单纯的勾勾嘴角。
“那是当然了。”他一字一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