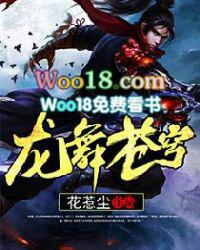三五文学>大宋道医免费阅读 > 8090(第6页)
8090(第6页)
“介甫,你差不多就行了。”曾巩磨牙道。
“好吧。”见曾巩态度坚决,王安石心知再继续下去,连那本《囿芸旧闻》都要被收回,只好遗憾作罢,“进去吧,让我试试阿衡亲手做的肥皂团。”
五岳观内,曾巩前脚拉着王安石去公共浴堂洗沐,后脚就有一位自称是国子直讲的官人来访,说是拾到一篇文章,想要物归原主。
“这位官人,您来得不巧,介甫兄刚刚离开。”清风与贵生道人跑去桑家瓦子看表演了,半天都没回来,苏衡正打算出门把那两人喊回来,就听见那瘦瘦高高的官人与看门道士的对话。
“看来无缘,只能等下次了”,那瘦高官人微微叹气,又问,“请问苏衡,苏小大夫可在观中?”
苏衡停下脚步:“这位官人您找他何事?”
“苏道长于在下有恩,此次入京,我想当面道谢。”那官人道。
嗯?苏衡打量了对方几眼,确定自己之前没见过这人,便道:“我就是苏衡。敢问官人名讳?我们之前似乎并未见过,不知您说的‘有恩’指的是?”
瘦高官人闻言,笑道:“原来小道长便是苏小大夫。前些日子,苏小大夫还为在下的义父按摩肩颈,义父近来感觉肩颈舒服了许多,不再隐痛了。”
义父?苏衡回想,自从韩琦与欧阳修离京后,他就只为庞籍做过推拿……
“您是司马官人?”苏衡微微惊讶,司马光何时入京了。
司马光点头,郑重道:“拙荆曾病重无医,多亏苏小大夫所赠之药才捡回性命。救命之恩,必铭记于心。”
有客人来访,苏衡不便离开,只好拜托一位师兄去桑家瓦子把玩疯了的贵生道人和清风捉回来用暮食。苏衡自己则把司马光请到了会客的茶室。
一番交谈后,苏衡得知,原来司马光在服丧结束后,便奔赴延州,投奔庞籍。后来,庞籍升任枢密副使,离开延州入京。司马光也于今春得授大理评事与国子直讲一职,上个月才到任。
司马光与曾巩同龄,却早早考中进士,而曾巩还在太学读书,年复一年地备考科举。司马光担任直讲,在太学授课时也注意到了曾巩这个学生,对他颇为赞赏。
“子固策论写得极好,没想到他所交友人也不遑多让,甚至还略胜一筹。”司马光感慨道。
“介甫兄任免回京述职,如今正在等朝廷安排,算是赋闲在家。他平日不是在家中读书,便是去太学或本观找子固兄交流学问。”苏衡道。
“是个好学之人。”司马光不住点头。
嗯,还是你未来亦敌亦友的死对头。苏衡心道。
熟药惠民局身为官办医药铺,因为每年都有户部补贴数十万钱,药价比一般市价要低上三分之一。住在外城的百姓经济情况往往不如内城百姓,因此大多喜欢到各大熟药惠民局买药看病。苏衡所在熟药惠民南局时不时还开展义诊活动,免费为附近百姓看病、开方与派药。
但达官贵人们看病,往往不会去熟药惠民局,而是找金紫医官看诊,买药一般也是去金紫医官们开的药铺。
从马行街一路往北,至到旧封丘门,道路两边除了香药店铺和官员宅邸,便是鳞次栉比的金紫医官药铺。这些药铺都是宫廷医官开的,并且根据各自擅长的病症,细分为很多“专科”药铺,比如若要治疗骨伤,则有大骨傅药铺,若要采买治耳聋、耳鸣的,以“独胜元”的杜金钩家和曹家两家药铺最为出名。除此之外,还有专卖口齿咽喉药的山水李家,以儿科闻名的班防御家和柏郎中家,专攻产科的任郎中家……不胜枚举。
因此,知道熟药惠民南局有位十三岁的苏小大夫的,大多是住在外城的平头百姓。但贵生道人给苏衡布置的出师任务,却是要名扬整座开封城。就在苏衡开始琢磨,是否要在内城以自己的名义开一家医馆时,来自邓州与眉山的信件竟不约而同地送达。
从邓州寄来的书信是范仲淹父子写的。去年冬,因宋夏和议已成,边防已固,范仲淹奏请卸下主持西北边防的重任,退居闲职。朝廷特批范仲淹迁往邓州居闲休养。
邓州富庶安然,离京师汴梁也不远,是元老重臣颐养天年的福地。开国宰相赵普、开国元老张永德、太宗朝的宰相苏易简都曾担任邓州知州,在邓州安养。范仲淹年离古稀之年还差之甚远,甚至还未到花甲之年,朝廷允许他知邓州,已是开了特例。
范仲淹先是带着长子范纯祐到了邓州,安定下来后,便将继室张氏还有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一并接了过来。一家人在邓州团聚,范仲淹也算得享天伦。
不仅如此,家中还添了一位新成员——幼子范纯粹。
等得空要去邓州看望一下范爷爷,顺道把粹儿的满月礼给补上。苏衡这般想着,把范仲淹与范纯祐父子的信叠起收好,继续看来自眉山的家书。
这次的家书怎么这般薄,之前每次都是厚厚一沓。苏衡微微皱眉,心中突然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第85章第85章归眉救亲
“清风,过来。”贵生道人刚步入五岳观中,便撞见清风,立刻把他唤了过来。
“师伯,您回来啦。咦?这是什么?”清风凑过去想看看贵生道人手里提着地麻布袋里都装了什么新奇玩意。
昨夜下了场大雪,今朝雪霁天晴,贵生道人便出了门,至晚方归。清风见他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像是遇见了什么大喜事,不由猜测那麻布袋里可能装着什么新鲜吃食。
“在郊外林子里逮着了一只肥兔子。”贵生道人笑眯眯道,“把着兔子送去厨房,同他们说,今晚我们要吃拔霞供!”
清风眼睛一亮,疯狂点头:“好好好!”拔霞供哎!冬日里吃上一锅热乎乎
的涮兔肉,快活似神仙!
清风两手提着那麻布袋乐颠颠地往厨房跑。贵生道人则哼着曲儿,懒懒散散地找他徒弟去了。
拔霞供这道菜背后有个小故事。据说发明它的人不是厨子,而是一位书生。那书生冬日游武夷山,遇上雪天,在山中一户樵夫家留宿。雪大无处觅食,那樵夫家中只有半边生兔肉,还是昨日吃剩的。书生见状灵机一动,将那生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与川椒腌制,又把风炉安到桌上,倒入半锅水,等水烧开,便可以开动了。
书生与樵夫一同夹起兔肉片在开水里涮,涮熟后蘸着调味汁一起吃,满口鲜香。两人吃得正香,外头雪霁霞出,美不胜收。那书生诗兴大起,吟诗道:“浪涌晴林雪,风翻晚照霞。”于是,这道涮兔肉便有了“拔霞供”这个雅致的名字。
贵生道人以前带着苏衡到处游医时,也曾口述这道菜的做法,让苏衡做给他吃。没办法,他实在没有厨艺天赋,若让他来烹制这道菜,那兔肉十有八九会被糟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