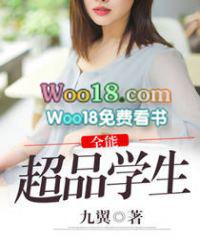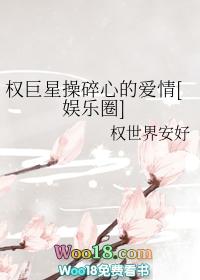三五文学>大宋道医35 > 4050(第10页)
4050(第10页)
贵生道人的医箱里头,一直藏着两个竹制的杯筊,很少见他拿出来打卦。今早不知怎的。贵生道人突然把那两个杯筊取出,在院中卜了一卦。苏衡在旁看着,也不知他向神请示了什么问题,最后的结果反正是一阴一阳,圣杯。
“不错!”贵生道人这下高兴了,收好杯筊就要带着苏衡出城。出城做什么?苏衡问他,他却卖起了关子,就是不肯说。
“乖徒儿,待会你就知道了。渴不渴?师傅给你买碗茶吃?”贵生道人笑眯眯地问。
“不必。师傅,我不渴。”苏衡摇头。
“两位道长,要来一碗茶解渴吗?现烧现泡,两文便有一大海碗!”从今早出来到现在还没开过张,卖茶人心里着急得很。茶叶倒还好,卖不掉留着还可以存很久,但这一壶壶茶汤烧开都是要烧炭的,这炭钱若是挣不回来,他便要折本了。于是,一见苏衡师徒走近,那卖茶人就卖力招揽起来。
“我徒儿不喝,那便给我来一碗吧。”贵生道人从钱袋里掏出两枚铜板。
“好嘞!马上!”如今八月初,秋风已起,天气微凉,那卖茶人头裹软巾,足蹬麻鞋,已穿上了长衫长裤,腰间还系着一条白色长汗巾。收了贵生道人的铜板,卖茶人微微弯腰,一手拿茶瓶,一手拿茶碗,给贵生道人倒了一大碗热茶。
茶瓶被卖茶人拿起,下面的炭炉就暴露了出来。原来,那炭炉就放在竹编的圆筐里头,竹筐底下放了个透空矮木架,设计倒也巧妙,高度刚刚好,卖茶人只需微微俯身便可拿起茶瓶,不必费力下蹲,透空的设计也能使得空气能流通,便于烧炭。
“师傅……”苏衡正欲说些什么,突然听见一阵的马蹄声从不远处传来,似春雷鸣响,一下下敲击着人心。他循声望去,只看见滚滚扬起的黄沙还有几面依稀可辨的旗帜。
“这阵仗,定是有大官爷要进城了。”卖茶人从旁边的小竹篓里用铁夹子夹了几块炭,添进炭炉里头,直起身随口说道。
大官爷?苏衡望着那越来越近的队伍,心下琢磨起来。这延州城最大的官便是延州知州张存,知州再往上,那便是——
距离越来越短,那支队伍终于从黄沙朦胧中现出真形。举着旗号官牌的旗牌官走在最前头开道,军士们骑着高头大马之跟在后头。那些骑兵披坚执锐,身上的铠甲在日光下反射着金光,簇拥着最中间一支队伍,也护卫着最里头那位长官的安全。好一副甲光向日金鳞开的恢宏场景。
苏衡目光一顿,他好像知道他师傅今早那一卦算的是什么了。
威严肃穆的队伍缓缓而行,城门周边的小贩们纷纷退避。等那支队伍进城远去,众人才重新开始做起买卖,吆喝声,还价声不绝于耳。
贵生道人已将那碗茶饮尽,他抹了抹嘴,将那粗陶碗还给卖茶人:“热闹也看过了,走吧,回伤病营。早则今日,迟则明日,被簇拥着进城的那位便会来营里巡视了。”
苏衡垂眸回想了一下,方才遥遥一望,那位大人被下属簇拥着,他只能隐约看见那位大人的清瘦板正的身形:“师傅,那位就是与您有一茶之缘的范大人吗?”
“不错。”贵生道人点头,与苏衡一道慢慢往城里走,低声道,“延州城怕是要变天了。我打听到,张大人的老母年事已高,近来入秋又犯起了老毛病。八旬老母重病难行,张大人又是个孝子,正为此忧心如焚。如今范大人一来,他终于可以脱身了。”
原来如此。苏衡眼神一闪,也不单单是因为母亲病重需要人侍奉吧。延州为边陲重镇,又经历了战火,如今城内一派萧条,百废待兴,延州知州这个位置谁坐谁头疼。
苏衡到延州,已有数月,这数月以来,也就见过张存两面。第一面是在知州府衙,那次是为了商议伤病营管事权一事,第二面是在伤病营,张存来营中检查改造的情况,结果自然是很满意。再后来,苏衡就没再见过这位知州大人了。
两次见面隔了不过半个月,但张存肉眼可见地消瘦憔悴了许多。不用想也知道,繁重的公务和与日俱增的压力压在身上,张存这位知州若是能睡得安稳,那才是怪事。
不过,这位范大人本身已是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着鄜延路的军务,若是代张存接任了延州知州,鄜延路财政军大权便集中于他一人之手。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位范公已年过半百,也不知身体是否吃得消。若是能有机会为他把把脉就好了,苏衡如是想。
康定元年八月,延州知州张存以母老需侍奉为由,请求调回内地。朝廷应允,将其调至泽州。范仲淹迁户部郎中,代张存知延州。
“延州交给范公,我便可安心离去了。”张存微微仰头,任由随侍的小厮为他系上挡风防寒的披风。行囊已于昨夜整理打点完毕,随时可以启程。
“听闻亲家公病重,亲家母离世,三女婿已辞官回家守丧。夏县地偏又不富裕,也不知三娘现今如何了,可有受苦。”张存踩上上马石,登上了马车。车夫问他行程,他沉吟半晌,打算先回家看望老母,再去夏县看看出嫁的三女儿。
张存共有一子六女。六个女儿中,长女、次女与三女均已出嫁。其中,张三娘最得张存喜爱,于前年被他许给了他十分看好的一位青年才俊。那青年年仅二十便进士及第,风光无限,被朝廷授官华州判官。只可惜,时运不济,初入仕途,便遭逢母逝,只好辞官居丧三年。
“倒是个大孝子,只是苦了三娘。”张存摇头叹道。
“大人,唐大夫与苏小大夫遣人送来一个包袱,说是临别赠礼,虽不是什么金贵玩意,但路上也许得用,希望您能收下。”有长随小跑而来,在马车外禀报道。
“哦?拿进来。”虽然只有两面之缘,张存对这对师徒却印象深刻。
他上任知州以来,虽勤勤恳恳,却也没有作出什么亮眼的成绩,只是平平。但伤病营的成功改革,却给了他灵感。边关军营都有这么一座伤病营,若是能总结出好的经验,在陕西各营推广开,也是一件功德。于是,那日亲自视察过后,他便梳理总结了延州伤病营的改造经验,往上递了折子,得到了圣上的赞许。这两位游方郎中,倒是他的贵人了。
原来,那日蔺太医一语道破贵生道人的前前任太医丞的身份,当时营中除了民夫与伤兵,还有韩军头与狄青。在贵生道人的强烈要求下,营内众人都向他保证,一定死守这个秘密,不与旁人言说。况且,贵生道人任太医丞的确已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旁人打听这个也没什么好处。因此,身为知州的张存一直以为贵生道人只是一位普通的游方郎中,顶多在民间有些名气。在折子上他也只提了“游方郎中
唐、苏二人“,并未引起朝中相公们的注意。
飘远的思绪拉回,张存低头打开那小包袱一看,发现里头都是一些便携的药丸、药膏,还有一张巴掌大的黄纸,上面详细写明了每种药物的用途,很是贴心。
张存心中熨帖,将这些药物重新包好,放入马车内的暗匣中,打算把这些药转送给女儿张三娘。夏县贫苦,想来医药条件也不太好,这些药送给三娘,图个心安也好。
张存没想到的是,这些药后来竟真的发挥了大用处,救了张三娘一命。为此,张三娘与她夫婿都默默记下了苏衡师徒的名字。此乃后话。
给张存送药是苏衡的主意。当初若非这位前知州大人的支持,他与师傅也不会那么顺利地就接管了伤病营。投桃报李,张存如今卸任离去,他们师徒多少也要表达一下心意。于是,便有了送药一事。
药一送出,苏衡便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在伤病营中给一位伤卒疗伤。
“苏小大夫,咱们这位新知州几时会来呀?这都快晌午了。”民夫丁五急得团团转。自打收到新知州要来军营巡视的消息,丁五就开始坐立不安,领着其他民夫又把伤病营的地面打扫了一遍,床单被褥也浆洗得干干净净。
“稍安勿躁。营里平时是什么样,便展现给知州大人什么样,不必过于紧张。小心过犹不及。”苏衡头也不抬,平淡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