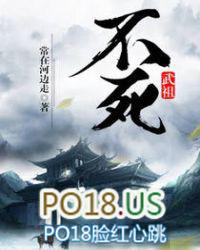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坏狗狗 > 第一章 伏笔(第1页)
第一章 伏笔(第1页)
科学研究表明,人对事物的记忆储存时间是有限的,当我去完整的回想我少年时光时,脑子里就只剩下了,一件破旧的宽大皮夹克,没有长熟的青枣,还有盛着红尾鱼的蓝色水盆。
而这一切,都跟我哥有关。
十五岁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我哥带我从山里的村子搬了出来,捏着养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点积蓄在镇上开了个打印店,以此来供我读书。
新租的院子不大,两间屋子,一间用来做饭吃饭,剩下那一间我哥在屋内砌了一堵墙,将房间一分为二,我俩一人一间。
阳光刺眼,我看着砖头墙面上布满的爬山虎,才反应过来我和我哥从那个破烂的山沟里出来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每日绞尽脑汁躲避养父酗酒后的殴打,睁开眼睛就是担心自己温饱,回洞之后抱着另一只老鼠互诉衷肠,另一只老鼠就是我哥。
我还以为我和我哥一辈子都会不见天日。
可初秋的一场雨,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清晨我和我哥去山上摘蘑菇,和拎着酒瓶子回家的养父擦肩而过,他回来给养母要钱,养母没给,他翻出来了养母唯一的积蓄,按照养母的话说,那应该是为我哥准备的老婆本,养母虽然脑子有问题,但是也知道护着那个钱。
两个人起了争执,养母失手把他推倒在了灶台上,然后自己也吞了农药。
我和我哥回家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气息了。
家里唯一的雨衣给了我,他穿着一件养父的破夹克,捂住我眼睛的时候我能闻见他手上湿泥土的气息,我透过指缝去看他的眼泪,突然意识到,我哥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大人了。
于是他开始像养母操持他一样去操持我,想办法赚钱供我上学,供我吃喝。
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天烧饭时候泪流满面的模样。
火光顺着他脸上蜿蜒的泪痕舔舐,远看像是昏黄夕阳下的恢弘港湾,下一秒就要有船只架起船帆远航,而他安静的犹如山间的坟包。
不见天日四个字又重新回到我脑子里。
我走过去抱住他的脑袋,雨水在外面打着,潮湿的气息顺着没关严的门缝钻进来,他窝在我怀里开始大哭,攀着我胳膊的力道很大,像是在生死间抓住了老天赐给他弥留的机会,我那时也在想,如果没有我,我哥也会跟着去死吗?
我轻轻拍着他的背,他的哭声像是漩涡要把我吞噬,他的眼泪我一滴一滴接着,如数家珍。
那年之后我仿佛是一个收藏家,勤勤恳恳的记着我哥掉眼泪的次数,我哥不算是个坚强的人,也总爱掉眼泪,他过的这么苦,要是再不掉掉眼泪,怕是要成死人了。
新租的院子外头有一颗枣树,栽在我们和邻里两家中间,所以枣树上的枣一家一半是我和邻居家儿子齐二苟从一开始就说定的。
暑假的一天晚上,我哥去给工头要账,我蹲在门口的石墩子旁等他,发现齐二苟踩着凳子,用小刀在我这边的枣树枝上刻记号。
他们家门灯坏了一个,光很暗,他压根没看见我。
我看着他的动作打发时间,几分钟后脚有些麻,我换了个姿势,一点动静让齐二苟回了头,隔着几颗青枣他盯着我。
“宋起。。。你,你怎么在这儿?”
听声音像是被我吓了一跳。
我捏着小腿问:“你干什么呢?”
齐二苟挺了挺胸膛,对于我这个外来户,他还是有几分底气的。
“宋起,我告诉你,这些枣树枝我都留下记号了,上头的枣都是我的!你要碰了你就死定了。”
我拍死一只蚊子,提不起来兴趣的“哦”了一声,迟钝的问:“为什么?”
原来是他喜欢上了一个同班的女生,吹牛逼说自家的枣子结的又大又红,等熟了要都送给她。
他讲的眉飞色舞,我的反应太小,引起了他的不满,他皱眉质问:“你没有喜欢的女生吗?”
确实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