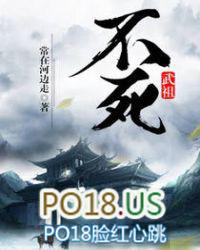三五文学>冯婉贞的结局 > 第2章(第2页)
第2章(第2页)
但本王还是小瞧了你,是不是?”
大晟有官学,三品以上官员子女可入学,但并非强制。
我十四五岁时,一日,父亲见我蓬头垢面从一根梁柱上爬下来,背上挂着好几面蛛网。
本应是闺秀淑媛的独女,变成个爬上爬下的野猴模样,平日母亲的怨言,在这一瞬的辣眼中终于落到了实处。
深沉的父爱就此觉醒,不久,他将我丢进了官学。
彼时,宇文驰不过是北雍道指挥使宇文铠的幼子,他从三品的爹,托了好大关系才让他留在京城的儿子入了官学。
官学如官场,攀上踩下,亦是势力得很。宇文家不过是北边僻境的兵油子,没人看得起,加之那时宇文驰身量未开,生得十分瘦弱,因而时常受人欺负。
欺负他的人中,就有我。
甚而,我是欺负他的人当中,心肠最歹毒,手段最恶劣的一个。
总之,在宇文驰的脑海中,这是根深蒂固的想法。
他将他天生的阴翳变态的根由,统统加诸在我身上,以此求得解脱。
卖入王府的第一夜,我被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万念俱灰地瘫在柴房的地上。
死志携着久远记忆悠悠潜入脑海,我和宇文驰的恩怨起因,早在官学时。
我有个自幼要好的闺中密友,户部左侍郎之女徐婉承,当年同在官学。
婉承小我两岁,生的婉约娇媚,一早便是个水灵灵的美人胚子。
那时节,常有些富贵登徒子守在女学署的垣墙外,只为捡着空子能瞅她一眼,婉承对此不堪其扰,甚而有了退署的念头。
一日她忽然哭得梨花带雨,在我的再三追问下,才说是让宇文驰拉了手,此身清白没了,只好将手砍掉以全名节。
“宇文驰?”
我花了好大劲才想起一个瘦小的身影,一时不敢相信,他竟有这色胆。
但印象中,他确实常躲在角落里偷瞄我们,眼神阴暗,让人一瞧便要起鸡皮疙瘩。
“一身铁锈和板鸭油味的宇文驰?”
婉承“噗”一声带着鼻涕笑了出来,继而又低下脸,点了点头。
宇文驰身上的味道确实呛鼻,引得同窗都对他避而远之。
据说那时他爹为了补贴家计,给他安排了一个在兵部军营里给兵器防锈的活计,刀剑等铁器防锈须用板鸭油擦拭,以至于宇文驰身上长日有挥之不去的铁锈气和板鸭腥味。
我劝婉承莫要声张此事,又叫上几个平日父辈相熟的男署官家子弟,拿定主意替婉承报仇。
我们跟了宇文驰几日,摸清他入学及归家的线路,“举事”这日午休,他们在学中布置,而我负责引开他。
我换上男装,叫住了独自在教塾门前晃悠的宇文驰。
“冯贞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