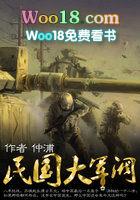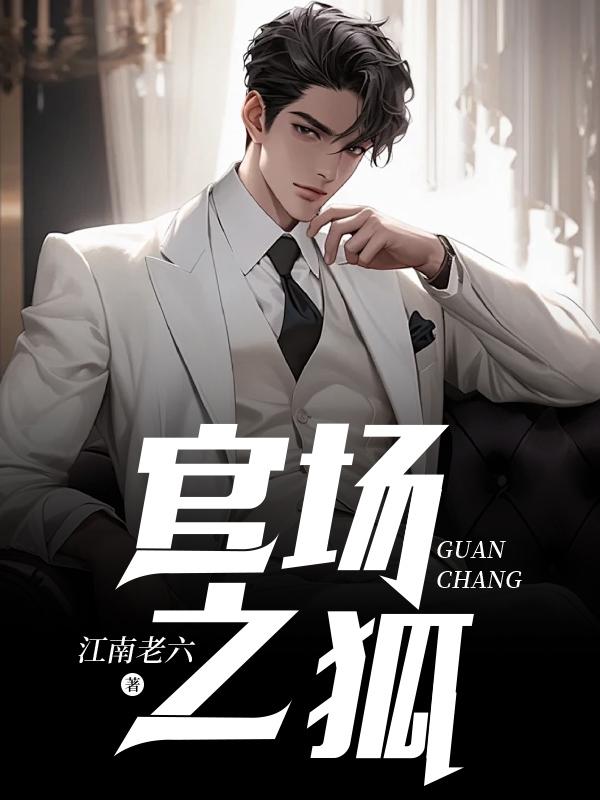三五文学>重生后前夫成了我的真爱 > 在床底(第2页)
在床底(第2页)
明春拎着铜壶回来后,李韦秋已将大大小小的药膏玉瓶和一些上药的器具摆在身畔的小几上。
他将铜壶放在炉上,不多时,等水开了,明春先他一步用钳执壶将热水倒在铜盆之中。
两人相对而坐,无言,小几上一灯如豆。
不知过了多久,李韦秋低头摸了摸铜盆,同她说:“水凉了,姑娘先在铜盆中将腕部的血迹洗净,再用绿瓶中的药粉撒在伤处。”
明春咬着唇忍痛按他说的做,又接过他接来的绷带。
他耐心地将桌上的几瓶药一一讲清用处,白瓶是活血化淤的丸药,绿瓶是止血的药粉,黄瓶用以止痛,粉盒内是除疤的膏药,伤口愈合后涂抹在表面即可,说完还反复嘱咐她千万莫要沾水。
“明日穆妍会派人送你回杂役院。”他说。
“多谢大人。”她心绪不宁本想就此告辞,李韦秋却坚持要送她回房间,只好揣着一堆药同他在月下庭院里又走了一遭。
回到房间,明春心有余悸地坐在床边,右手抚上心口,其间扑扑跳跃不止。
她恨自己心性不坚,又险些被李韦秋毫不刻意的好与美色蛊惑,实在防不胜防。
曾经如此,当下亦是如此。
他就像山中精怪,用这些世人奢求的镜花水月蒙蔽她的耳目,同她交换了一颗真心。
她暗暗唾弃自己,父仇未报,尚未明晰的敌人就在眼前,怎可卸下心神。
直至腔中澎湃热涨的心渐渐平息,她才想起躲在床下的鱼拓,低头唤了几声,无人应答,再往床下探头,原来她已经走了,于是合衣躺下,一夜无梦。
翌日,明春天未亮就起来收拾,想着李韦秋说今日穆三娘会遣人送她下山,早早地等在门口。
大约辰时二刻,外间就来人了。
明春赶忙打开房门,没想到的送她下山的人竟是孙兼令。
她朝孙兼令行了礼,后者好整以暇地将她扶起,笑意盈盈:“我记得你,那日在杂役院多亏了你,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明春。”
明春是坐着竹轿被人抬回杂役院的,山路陡峭崎岖,尤其到了拐弯处,人像是从悬崖上支出去了似的,她两手紧紧抓着横栏,心里时不时替抬竹轿的四人捏把汗。
有她作对比,孙兼令显得稳坐如山,她扶着扇子,一双明如秋水的翦瞳躲在扇面后头,凑近明春,用气声道:“听三娘说你上山替她办了件了不得的大事。”
她话只点了一半便不再说了,明春有些犯难,不太明白孙兼令究竟是何用意,想着昨晚鱼拓的提醒,又害怕给穆三娘惹上麻烦,深思熟虑之后,只对着孙兼令尴尬笑了笑。
孙兼令自是解语,丝毫不恼明春的不善观色,朝她摆摆手后就靠上腰枕阖眼小憩。
一旁的明春就不甚惬意了,她此刻实在是无福享受翠岐山这无几人有的待遇,直直地挺腰,缩着脖子如坐针毡。
现下虽刚清晨收露,却也顶着朝阳,不过片刻她的额前就沁出了一层薄汗,更别说底下四位扛轿的人,他们发髻和领巾早已湿透,再一念及昨日自己上山的模样,明春握着横杆的手紧了紧。
上山难下山易,约莫半个时辰,一行人就到了杂役院。
竹轿颤巍巍地落地,孙兼令也醒了,她朝明春伸手,明春赶忙上前扶着她下了竹轿。
孙兼令凑近她耳语:“切莫提及三娘的名号。”
她恭敬垂首:“小人明白。”
明春扶着孙兼令的手进了杂役院,一路上许多杂役递来试探的目光,她心虚得头也不敢抬起来。
郑观堤合手站在杂事房前等着她们,二人到了之后,她先是扫了明春一眼,又看向孙兼令:“兼令这是?”
孙兼令揽过明春,笑叹道:“郑管事有这么个能人怎么不早说?我寻了好些时日的字帖,没想到明春就写了一手的漂亮字。”
“昨夜我特意留她给我写了几篇,此刻定是累极了,便因着我,郑管事这几日也得少给她安排些活计。”语罢她朝明春挤挤眼,“昨夜受累了,今日活计就先免了,快去歇息罢。”
“是。”明春看了看郑观堤,后者颔首,朝二人行礼后回了杂役通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