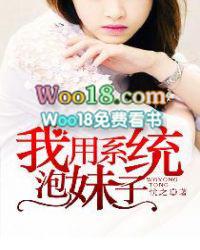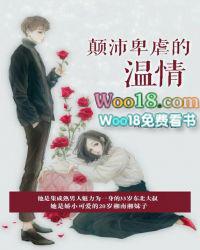三五文学>书签中间一个空啥作用 > 三十九 书与微光(第2页)
三十九 书与微光(第2页)
骆嘉怡听懂了,没有反驳,反而笑了一下,眼里是她一贯熟悉的倔强:
“可事情没到最后,谁也说不准。”
“只要还没定下来,就还有变数。我不想以后回头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
她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沈瓷,语气温柔又直接:
“你不用劝我。我这次,不想做那个退让的人。”
沈瓷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默默接纳她的所有决定。
“我能帮你做什么?”
骆嘉怡顿了顿,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折页本,翻到一页,推到沈瓷面前。
纸上是一幅速写,线条干净、节制,是一条羽毛形状的项链,细节柔和却极有辨识度。
“帮我看看,”她说,“圈子里有没有谁戴这条项链。”
“我凭记忆画的,大概有七八分像。”
沈瓷拿起画,仔细看了一会儿,眼神里多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凝思。
“我会留意的。”她点头,语气笃定。
“你放心,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与此同时,就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端,一段安静日常的生活,正在缓缓展开。
祁祺结束了连续十几天的海外拍摄行程,回国后的日子终于短暂松了口气。
这几天,剧组进入技术调整期,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久违的“空档”。
周末,他约了刘奕羲,吃她那顿“版税庆功宴”;其他时间,他像往常一样,回了趟家,打算陪父母住几天。
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每次工作间隙,他总是会第一时间回家——那里不喧闹,也不需要他时刻调整状态,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喝茶、翻书,像回到另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区。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地方,那些镜头下无法安放的情绪,才会悄悄松开一角,露出真实的模样。
客厅还是熟悉的布置,沙发上搭着母亲新买的浅蓝色靠垫,茶几边沿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本杂志和书。
其中一本封面略显厚重、印着山路与风旗图案的书,赫然是《风起之路》。
祁祺扫了一眼,唇角带笑地摇了摇头。不用猜,他也知道是谁买的。
——准是他母亲林芷兰。
从小时候他在学校演出开始,到后来上综艺、接剧本、拍电影,母亲从来不说什么鼓励的大话,却总能在家里默默出现那些相关的海报、剪报,现在换成书了,风格也没变。
他走过去拿起那本书,翻了几页,书页边角还夹着一张刚撕下的便利贴,上面写着一行工整的小字:
【写得挺细的,到这儿先停一下。】
字迹不大,但工整清楚,像是读到某个片段时随手记下的小注脚,没有落款,也没有多余情绪,却透着一种低调又温柔的陪伴感。
祁祺盯着那张便利贴看了两秒,没说话,只是微微弯了下唇角。
祁祺望着那句话,神情柔了几分,重新合上书,轻轻放回茶几上,然后站起身,朝厨房的方向边走边喊了一句:
“妈,中午吃什么?我来帮忙了。”
厨房里响起母亲熟悉的声音:“你啊,回来就想抢我手上的活。”
祁祺一边走进去一边笑:“那可不行,我这段时间可是没摸过锅铲的人,得补上点儿手艺。”
厨房里已经飘出淡淡的姜蒜香,母亲在切菜,父亲站在一边择菜,两人一边忙一边还拌着嘴,话不多,但气氛松弛自然,带着家的气味。
祁祺挽起袖子走过去,熟练地从刀架上取下一把刀,“来,我来切这盘西蓝花。”
母亲笑着让开了位置,一边洗菜一边说:“你别忙活了,回来就歇着吧。你这段时间不是连轴转嘛,好不容易有几天清净。”
祁祺嘴角扬了扬,还是走过去拿起了菜刀:“正好手痒了,想切两刀过过瘾。”
父亲也从一旁抬起头,看着他:“行了,你妈说得对,你这难得回来一趟,还是多歇歇。”
祁祺弯了弯眼角,没接话,只是低头切菜,刀落在案板上的节奏均匀有序,仿佛一切都刚刚好。
切菜声、锅铲翻炒声、父母轻声的闲聊声,在厨房的烟火气中缓缓交织,构成了一个他最熟悉、也最安心的午前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