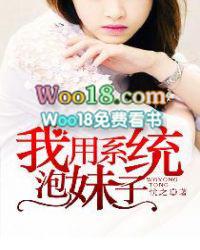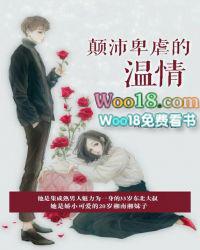三五文学>载我以形 劳我以生 > 洛神赋六(第2页)
洛神赋六(第2页)
祈福法事,自然是为昭示天命,稳定朝野,凝聚民心。
玉虚宫山门之外,早已是人头攒动,万民翘首。
神策军士兵维持着秩序,划出宽阔通道,数十口巨大的铁锅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下支起,灶膛里柴火熊熊,锅内热气蒸腾翻滚,散发出混合着麦香与油酥的甜香。
一块块烤得金黄酥脆、足有脸盆大小的胡麻饼被铁钳夹出,带着滚烫的热气,迅速被分切成规整的小块。
道观中手脚麻利的坤道与俗家门生,穿着整洁的青色短褂,排成长龙,将切好的饼块用以干净油纸包好,再经由神策军士兵之手,一包一包,秩序井然地分发给队列中的百姓。
“领饼喽!楚王殿下赐福,玉虚宫施饼喽!”洪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多谢殿下!多谢道长!”领到热饼的百姓,无论是衣衫褴褛的贫者,还是带着孩子的妇人,无不喜笑颜开,紧紧攥着那包着温热食物的油纸,不住地朝着山门方向作揖道谢。
孩童们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烫得直哈气,小脸上却洋溢着纯粹的满足和欢喜。
空气中弥漫着烤饼焦香,胡麻醇香。
与此同时,紫霄宫侧门处的杏林阁药局,三扇厚重的木门也已完全敞开,门楣上悬挂着崭新的“奉旨施药三日”的朱漆木牌。
药局内,浓郁而复杂的药草气息扑面而来。一排排高大的乌木药柜前,十数位道观内精通医理的坤道坐诊,为排队的百姓诊脉。
更多的道童和药工则穿梭忙碌于巨大的药柜与碾药、煎药的区域之间。
靠墙的长条案几上,分门别类地堆满了包好的药包,其上分别贴着红纸标签,写着“风寒散”、“消食丸”、“祛湿汤”等字样。
“奉楚王殿下恩典,玉虚宫杏林阁开仓施药三日!凡长安百姓,无论户籍,皆可凭号牌领取对症成药一剂!”负责维持秩序的知客道长声音洪亮,清晰地传遍人群队伍。
队伍蜿蜒漫长,多是些面带病容或衣衫单薄的贫苦之人。
他们手中紧紧攥着方才在山门外领到,写有编号的竹签号牌,眼中充满了感激与期盼。
“无量天尊!诸位道长真是活神仙啊!这风寒药,可救了我家郎君的命了!”一个老妪领到药包,激动得语无伦次,不住地朝着药局内供奉的三清神像方向鞠躬。
“多谢殿下!多谢道长!”感激之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温热声浪。
清和堂的素宴,也在这片象征与民同乐的声浪中接近尾声。
萧允仪率先起身,侍从立刻上前为她整理绛袍珠冠。
她目光沉稳,扫过堂内众人,最后在裴照野身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深邃难明,随即恢复了一贯的威仪,在仪仗簇拥下离去。
萧允贞也随之站起,动作带着一丝慵懒的随意。他并未再看裴照野一眼,好似那支金钗不过是他随手丢弃的一件小玩意儿。华贵身影在尉迟墨雪的随侍下,很快也消失在通往内苑的侧门。
清和堂内紧绷的气氛终于彻底松弛下来,低语声变得清晰,官员们开始互相寒暄,陆续离席。
裴照野依旧端坐原地,周遭的视线或明或暗地扫过她发髻的金钗,侍立在她身后的青梧立刻上前,将一件厚实的玄狐大氅轻轻披在她肩上。
那些低低的、刻意压制的议论声浪如同蚊蚋,嗡嗡地钻进耳朵:
“……瞧见没?这安阳郡君果真浪荡疯癫,你家女郎也快到娶夫的年纪了吧,可别摊上这般货色。”
“裴家女郎这步棋,走得真狠,连颜面也豁出去了……”
“……呵,一个残废,一个疯子,倒真是般配……”
“嘘,慎言!没看楚王殿下的脸色么?这分明是……成了!”
裴照野置若罔闻,微微抬手,指尖触碰到了发髻间那支冰冷的螭龙金钗。赤金的龙身盘绕,龙口衔着的珍珠贴着她的鬓角,分量足够沉淀。
她算是彻底成了件皇室的物样,萧允贞替她铺平了路,却是以这般无有体统的方式,她自幼习礼,一向在女男之事上洁身自好,当众被男子如此狎昵地簪钗,礼法尽丧,羞愧难当。
也罢,裴照野的颜面,早已在坐上轮椅那日便失得一干二净。
萧允贞此举虽放浪形骸,却效果绝佳,裴氏与楚王府的关系,不久自会为天下人所知,省却了她无数口舌周旋。这支金钗,不过是她目的达成的象征,是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倘若真能撬动崔氏,替母亲雪冤复明,再续裴氏公卿门楣,这点体面又算得了什么。
指尖下,冰冷的金饰棱角分明。裴照野缓缓收拢手指,用力地攥紧了轮椅的扶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微微颤抖着。
山门外,百姓领饼的欢呼声浪,隐隐约约,带着些许人间烟火,不断涌入逐渐寂静下来的清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