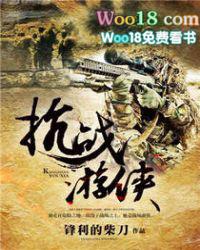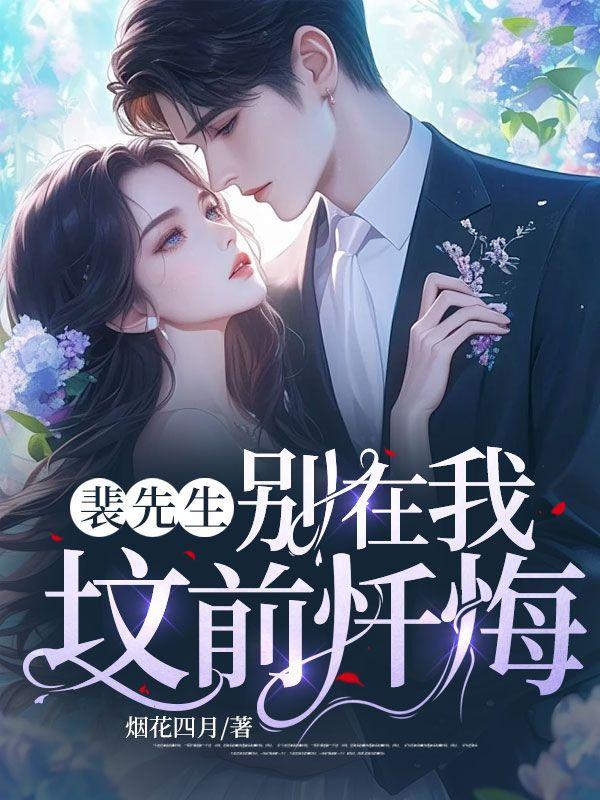三五文学>大秦帝国献公 > 192章 降将的算盘与狼崽的隐忍(第1页)
192章 降将的算盘与狼崽的隐忍(第1页)
北疆的风,似乎带上了某种宿命的味道。
几名在战争初期便审时度势,率部投降,并为秦军引路有功的匈奴小部落首领,此刻正享受着秦军许诺的宽大处理。
他们被允许保留一部分部众和财产,在指定区域放牧,只是那无处不在的秦军巡逻队和罗网密探,如同鹰隼般时刻盘旋在他们头顶。
其中一个名叫呼都尔的部落首领,脸上堆满了谦卑的笑容,对前来慰问的秦军校尉点头哈腰:“将军放心,呼都尔一定约束好部众,为大秦戍边效力,绝无二心!”
他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去那些俘虏营中,劝说那些冥顽不化的同族安心为大秦服务。
蒙恬对此不置可否,只命人好生照看这些识时务的降将。
秦军确实需要一些这样的模范,来瓦解被俘匈奴人的抵抗意志。
很快,呼都尔便带着几名亲信,出现在各个劳动营和奴隶安置点,用匈奴语痛心疾首地讲述着“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道理,劝导众人接受现实,为大秦劳作,争取早日获得新生。
有人被他说动,眼神中露出一丝活下去的渴望;
也有人面露鄙夷,暗骂其为鹰犬走狗。
罗网的密探将这一切都记录在册,对呼都尔这类降将的监视,从未放松。
他们深知,草原上的狐狸,即便披上了羊皮,也难改其狡猾本性。
暗地里,一些降将之间眼神交错,传递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讯息。
草原上血腥的净化告一段落,但帝国的机器一旦开动,便不会轻易停歇。
在某处新开辟的矿山,昏暗的矿道内,火把摇曳。
一名负责监工的秦军老卒,见一名匈奴女奴颇有姿色,便起了歹心,上前拉扯。
那女奴平日里逆来顺受,此刻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抓起地上磨尖的石块,猛地砸向老卒的头颅。
老卒惨叫一声,脑浆迸裂,当场毙命。
女奴还未及反应,便被闻讯赶来的其他监工乱刀砍死。
她的尸体被高高挂起,以儆效尤。
然而,她那短暂而决绝的反抗,如同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在其他匈奴奴隶心中,激起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涟漪。
草原启蒙学堂内,朗朗的秦语读书声回荡。
数十名匈奴孩童,穿着统一的秦式短褐,正跟着秦人士子学习《孝经》。
一些孩子已经能用略显生硬的秦语与教官对话,甚至开始模仿秦人的礼仪,似乎已经渐渐淡忘了自己草原儿郎的身份。
教官们对此颇为满意,认为秦化教育已初见成效。
人群中,那个名叫阿茹娜的匈奴小女孩,依旧抱着年幼的弟弟,显得格外安静。
她学习秦字秦语异常刻苦,甚至主动帮助教官管理其他孩童,分发食物,俨然一副模范学童的模样,深得教官喜爱。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她会悄悄躲到无人注意的角落,借着月光,用磨尖的指甲,在土墙上歪歪扭扭地刻下一个又一个匈奴名字——那是她死去的阿父、阿母、兄长以及族人的名字。
刻完一个,她便用舌尖舔去指甲上的泥土,眼神中没有泪水,只有与年龄不符的、如同草原狼崽般的幽深与冰冷。
她怀中的弟弟,似乎也感应到了姐姐的情绪,在睡梦中发出不安的呜咽。
咸阳,治粟内史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