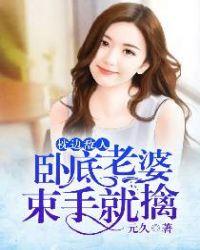三五文学>抗清战争 > 第412章 汉复再不复汉更待何时(第1页)
第412章 汉复再不复汉更待何时(第1页)
淮安,运河重镇,明朝时在此设漕运总督,为江北第一大城。
清军入关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省下又设四巡抚,即驻淮安的凤庐巡抚、驻安庆的安徽巡抚、驻苏州的江宁巡抚,驻池州的操江巡抚。
改江南省以来,四巡抚时常变动,凤庐巡抚和安徽巡抚曾一起被裁,辖区由漕运总督管理,不过在顺治十七年因漕运总督难以兼管,又复设凤阳巡抚。
此间操江巡抚也曾裁撤统为安徽巡抚。
康熙三年清廷欲拆解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如此只设江苏巡抚和安徽巡抚即可,然因西山战事原因导致江南省一时无法拆解,结果便是仍维持三巡抚制。
长江以北以驻淮安的凤庐巡抚为主,江南则以江宁巡抚为主,原江南左布政(安徽)以安徽巡抚为主。
现任江宁巡抚是汉军正红旗出身的韩世琦,安徽巡抚是汉军正蓝旗出身的张朝珍,而凤庐巡抚则是几年前在江南利用“奏销”、“哭庙”、“通海”三案,将江南士绅杀得人头滚滚,多少人家为之灭门破户,得了个“朱白地”骂名的朱国治。
朱国治被重新启用同当初西山战事反复有关,由于王五的出现让围剿西山的清军损失惨重,八旗的底裤更被扒个精光,搞的燕京满城家家带孝,用于平定明朝最后力量的军饷也由起初的六百多万两一下提高到千万两。
就这还不够,因为战事规模已经扩大,受到战争波及的地区不再是一座连一县之地都不及的茅麓山,而是变成了大半个湖北。
户部疲于奔命,国库已经陷入困难境地,为此时任户部尚书的马尔塞私下建议鳌拜在江南地区再开一次“奏销案”,好解当前燃眉之急。
鳌拜欣然同意,命人将被革为平民的朱国治召入京中,拟重新调任江南为朝廷搜刮钱财。
但朱国治在江南名声太臭,任命遭到两江总督郎廷佐强力反对,加之江南三大案发生才几年,清廷要是再次竭泽而渔恐会令江南士绅再起反心。
毕竟,当时湖北的战事已经蔓延,尤其被清廷招降的王五在荆州一次杀了数万旗人,丢入江中的旗人尸体甚至都飘到了长江下游,到处都是明军卷土重来的小道信息,搞的人心惶惶,给人一种清廷统治不稳迹象。
江南地区本身也是反清最激烈的战场,几年前郑成功还领大军进入过长江,民间士绅对满清统治都是不满,只是因为清军屠刀太利,郑氏大军惨败,这才让江南士绅不敢轻举妄动,但暗中为反清复明提供资金和舆论支持的却是大有人在。
如那去世的文坛领袖钱谦益。
要是清廷统治稳固,江南士绅可能就认命了,现在反清的明朝余部将局面又打开,险些被郑氏大军活捉的两江总督郎廷佐自然担心重启朱国治会激起江南民变。
江南要是再乱,这大清朝可就真的没救了。
郎廷佐的反对起到了效果,无奈之下鳌拜便让朱国治先到淮安任凤庐巡抚,准备合适时机再让其到江南去刮钱。
到任淮安没多久,就传来吴三桂起兵造反消息,以大清忠臣自居的朱国治自是将吴三桂骂了个狗血淋头,还上书要求杀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绝吴三桂子嗣后代。
这个上书清廷没理会,主要是当政的鳌拜觉得吴应熊父子还有利用价值,关键时候说不定能拖一拖吴三桂,未想前线刚传来吴三桂死讯,宫中的小皇帝就迫不及待将大清的定海神针鳌少保给扳倒了。
鳌拜的倒台把远在淮安的朱国治吓坏了,担心朝廷把他当作鳌拜党羽给办了,匆忙将历年搜刮的钱财送到燕京打点,尤其是鳌拜案的主审官康亲王杰书那里更是砸了重金,一通操作下来总算暂时平安落地。
钱没了可以再搜刮,可大清没了那就真的什么也没了。
自知在江南作孽太多的朱国治也是无心政事,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前线战事,等到传来吴三桂死讯,吴军方面拥立吴三桂的孙子称帝改元洪化消息,这位巡抚大人不禁仰天长笑,觉得真是天不亡大清。
没有了吴三桂那头猛虎,吴军再强也不过散沙。
事实上也确如朱国治所想,吴三桂的死迫使渡江的吴军主力龟缩,一些原本投降吴军的官员暗中也开始动摇。
一心想为大清再立功勋的朱国治则是如打鸡血般,不遗余力搜刮江北数府钱粮供应正在庐州和凤阳一线对抗吴军大将吴国贵的江南提督梁化凤,还勒令各地强拉壮丁充军,拼凑了两万多人马沿运河布防,防止吴军窜入江淮地区。
闽浙和江西方面也是捷报频传,然而就在朱国治以为局面重新利好大清时,燕京沦陷的消息如同一记闷棍砸了过来。
消息是沿运河传来的,传播消息的载体就是那些奉命运粮到北方的漕工。
在这些漕工的传播下,燕京沦陷,八旗被屠的消息跟插了翅膀似的向各地飞传。
传的可吓人了,说吴军把旗人一队队的往城中海子里赶,能活埋就绝不浪费弓弩火药。
又说把那些汉官汉奸削鼻子的削鼻子,砍四肢的砍四肢,抽筋扒皮无所不用其极。
也不知谁造的谣,说吴军把范文程等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臣给丢进大锅活煮了,死了的洪承畴也被挖出来吊在城门示众。
燕京沦陷消息应是属实了,因为朱国治派去打听消息的人到了山东临清就过不去了。